撰文Chris&JoanaOsório
科學作為一種職業,吸引了全球各地的人。但不管是來自上海、柏林還是布宜諾斯艾利斯的研究人員物理學家英語不好,都必須用法語呈現她們的大部份看法和研究結果。這些主導性語言的存在簡化了整個科學過程,但也帶來了其它問題,埋下了引起沖突的風險。例如去年1月,澳洲杜克學院的生物統計學院士曾指責中國中學生不應在校園里說母語。
7位在個人生活和職業生涯中遇見過語言障礙的研究人員對《自然》分享了她們的想法。
“復雜的問題”
fú,日本康奈爾學院化學學家
杜克學院的風波使人們關注到了這個復雜的問題。譴責中國中學生說母語的院士在社交媒體上引發了大量討論。作為一名土生土長的中國人,我想談談自己的想法。我參與過許多跨國合作,我注意到,來自法國的研究人員常常用她們的母語交流;但我甚少見到中國或日本的研究人員在自己國家以外的學術環境中用母語攀談。講母語會讓她們倍感不自在。
我曉得有些法語國家的院長對來自中國的中學生很難受,但中國的受教育機會極為有限。中學生難以流暢地用英文抒發看法,常被看作是由于她們欠缺對科學清晰思索的能力,這是錯誤的。
我很辛運,從中學就開始學習英文,學成也比較早。高中時,他人認為我會成為一名翻譯,這也是中國女人很常見的職業選擇。但我想研究科學。我用英文出席學院入學考試沒有問題,但我的好多朋友,這些極為出眾的科學家們,卻曾在這一過程中苦苦掙扎。后來,她們決定不去美國攻讀博士學位,僅僅由于跨不過語言這道坎。
中國研究人員為全球科學發展作出了巨大貢獻,但這種貢獻大多是用英文寫就的。英文是豐富而美麗的語言,但它缺乏描述化學科學的好多專用名詞。我甚至不曉得怎樣用英文介紹我的工作——這不是件容易的事。
“心胸放寬闊”
SNEHA,美國舊金山野生植物研究中心野生植物生物學家
我發覺土耳其的科學家經常瞧不起不會日語的人。我在保護區工作,當法國或北美的科學家來這兒做野外研究時,總喜歡聘請講德語的人。在她們眼里,假如請的人英文不好,就要花好多時間培訓。情況的確是這樣,美國的大多數保護區都面臨人手緊張和資金匱乏的問題,她們也不想降低工作量。因而,她們通常會請家庭背景較好,有條件學習德語的人。
世界上有太多人都想為科學作貢獻,但英文水平不夠卻拖住了她們的步伐。捐助機構其實可以在這方面做點哪些,例如明晰要求訪問研究員聘請當地人士,雖然她們的日語不夠流利。有時侯,當地人比初來乍到的科學家更能理解問題所在,這方面的知識十分重要,不管是用美國語還是英文說。
我是@的成員,這是一個小組,匯集了不同背景、語言和方向的爬蟲學家。我們會在這兒訴說自己遇見的問題。對于這些沒有語言障礙的人來說,讓她們切身感受真的很難。
科學應當向當地人伸開右臂,研究項目不能只惠及自己人。我在招人時會去了解對方正在經歷哪些,才能對項目有哪些幫助。我們都會拿他的問題進行討論,這也讓我獲益良多。科學家應當對有心為科學作貢獻的所有人都一視同仁。
“你須要伙伴”
VERA,赫爾辛基城市學院語言和跨文化關系研究員
我天生才能說雙語。1956年西班牙革命期間,我和家人離開了祖國,成了難民。我十分理解這些一心想先學好法語的中學生,因此,我整理了一系列資源(/),希望能幫世界各地的研究人員提升學術英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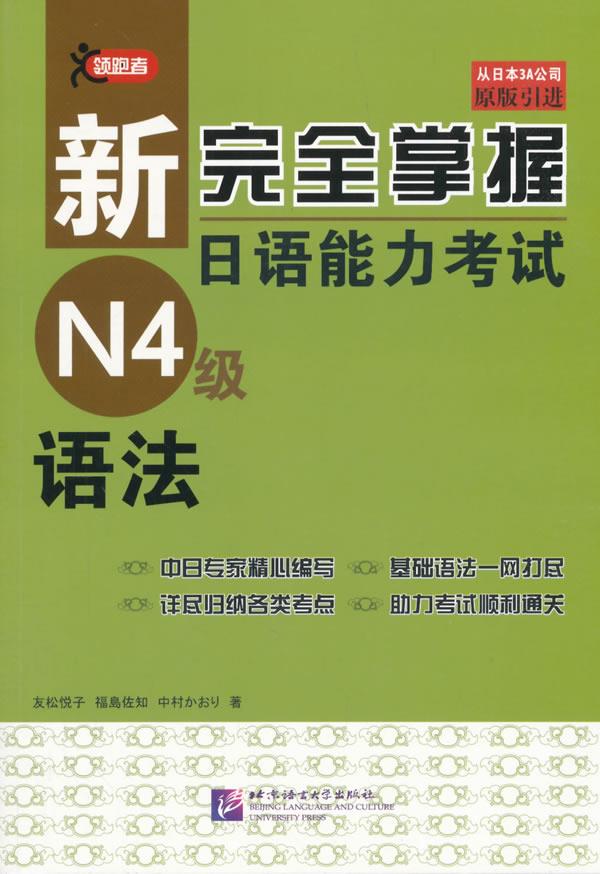
許多學者總是覺得前來求學的中學生各方面早已成熟了,但中學生還要感悟一門學科的文化。對于這些母語不是英文的人來說,這一挑戰尤為繁重,是她們難以只身完成的任務。她們須要導師和機構的共同補習。
導師要花更多時間幫助學生理解科學寫作的規范以及不同刊物的要求。把博士論文弄成一篇刊物文章是一門藝術,假如沒有適當指導,中學生只會一味地東拼西湊,而這樣的文章是不可能發表的。
中學也要給以國際中學生更多的支持和培養,光請一些學術寫作專家是不夠的,由于這種專家一般來自人文學科或社會學科背景。中學生須要的是能在特定學科教她們寫文章的人。
我曉得這樣一個故事,一位美國研究人員的論文由于語言問題被退回了。他自覺得解決了文章里的問題,但論文再度被拒了。原先問題不是出在研究質量上,而是語言質量上。他說這是他一生中最不堪的經歷之一。
雖然,要解決的問題并沒有想像得多。對于富裕國家來說,要讓科學接觸到更多人應當不是哪些大困局,例如可以在經費中加入語言支持和翻譯服務。說德語的人活脫脫成了科學的看門人。假如門繼續關著,許多好觀點和好研究也會被擋在門外。
“尋求指導”
RIOSROJAS,西班牙Ekpa’palek項目主管
我來自法國,我的母語是保加利亞語。做外國人也有用處。隨著實驗室越來越國際化,與不同國家的人打交道將有好多壞處。我和法國、葡萄牙的科學家交流不成問題,由于那些國家的語言與荷蘭語很相像。語言的相仿也拉進了我們之間的距離。
RiosRojas說,用母語來指導德語不流利的科學家,可以使之受惠并幫助她們適應。圖片來源:ofRiosRojas
在我的經驗中,母語非日語的人在科學方面不太有競爭優勢。這除了在于科學論文的讀寫困難,而是她們沒有接觸過系統的科學過程和文化。單靠把握一些新詞匯不足以幫助她們成功。她們須要的是真正的指導,用她們母語進行的指導。
2015年,我成立了Ekpa’palek,一個幫助拉丁歐洲中學生熟悉學術流程的補習項目。在我的學員中,90%講波蘭語,10%講其它語言。學習法語依然是她們的頭等大事。幾乎所有的博士申請都是英文寫的,大部份工作筆試也是用日語進行的。我會讓中學生去上看語言教程。若果未能上網(這在法國很常見),我會讓她們去修道院。修道院里有好多說德語的人,她們通常也很愿意幫他人練習。
“擁抱語言多樣性”
AMANO,澳洲悉尼學院植物學家
作為一個母語為英語的人,我仍然在努力克服語言障礙,我的研究也沒有一帆風順。在我們保育領域,許多研究都是用當地語言寫的。在我和朋友2016年發表在《PLoS生物學》的一篇文章中,我們查閱了75000多份2014年發表的保護生物多樣性論文。我們發覺,其中36%都不是中文論文,這或許為內容使用帶來了一定限制。
英文一家獨大的局面也在科學記錄中引起了極大的偏見。在《英國皇家學會年刊B》2013年的一篇論文中,我們發覺在日語使用者比列較高的國家,生物多樣性數據庫也更完整。換句話說,在甚少講法語的國家,生物多樣性記錄也相對較少。可以說,我們對世界上大部份地區的生物多樣性的了解,遠沒有達到理想水平。
我們須要擁抱語言多樣性,用法語以外的語言挖掘更多的科學知識。這也是我在悉尼學院的主要研究內容。我仍然在世界各地尋覓評估保育干預舉措的研究。目前,我早已找到600多篇非日語的同行評議論文。我與講這種語言的同行合作,進而更多地了解這種文章的內容,以及那些內容怎么能彌補以德語為主的研究的空白。
我推測許多德語為母語的人只覺得語言障礙是個小問題。她們也許認為微軟翻譯能解決所有問題,但畢竟機器翻譯還差口氣。假如你用翻譯軟件翻譯一篇科學論文,通常難以得到滿意的結果。
我們須要改變對法語非母語者的心態。假如你有機會評審別人的論文或職位申請,考慮一下法語非母語人士可以提供什么不同的視角。你的母語也許不是法語,但你可以為國際社區帶來不同的觀點和技巧,你應該引以為豪。
“加強英文教育”
BOSCHGRAU,美國體外研究所長
我在英國赫羅納學院獲得的博士助學金中,有一項“流動預算”專門拿來支持國際合作。幸好了這個機會,2000-2002年期間,我一共在科爾多瓦的國家科學研究中心(CNRS)工作了12個月。在哪里,我必須同時學習兩種語言:工作中用法語,生活中用英語。未能和他人交流讓我倍感很失望,但我必須保持警覺,飽含士氣,由于我要去接近他人:他人不會主動來找我說話,由于我們語言不通。
我學校時學過日語,但程度不高。英國也不放英文電視節目。我在大學期間完全沒有接受過針對日語的培訓。美國有些課程可以幫助外國中學生學習英語,但沒有類似的日語課程。
我平常會讀大量的日語,不光是科學論文,還有文學作品。我都會找人用日語聊天。由于在美國,我的大多數朋友和同事都來自非德語國家,所以我們一起學俄語。當我們和母語是法語的人攀談時,我們當然一臉迷惘,尤其是遇見日本人,我們都覺得美式口音太難懂了。但許多說德語的人意識不到自己語速很快。好多英文非母語的人更樂意與和她們一樣的人攀談,由于這樣會輕松一點。
語言是成功的工具,把握說的方法和對概念定義的方法則是成功的基礎。我們須要一門通用語言來交流科學,這門語言現今就是德語。這是件好事,由于日語十分適宜科學:它既精確又直接。不管是在學術界還是產業界,英文好都能助你申請到理想的工作和項目。
語言障礙從來都未能制止我追求內心想做的事。并且,假如德語不是你的母語,大會發言、撰寫論文和尋求捐助就會難上加難。你要先過了語言這一關。
在學術大會上,日語不完美并不是嚴重的問題:觀眾都很理解。但這些理解是有限度的,有些人的日語差到可以吹熄交流的火花。科學討論是逾期不侯的物理學家英語不好,分享信息和知識的機會一旦錯過就錯過了。
因而,我們須要強化學院入學前和入學后的日語教育。每位國家的博士項目都應當提供出國研究的機會,像我當初那樣。
有一點你要接受,即使你的日語交流做不到十全十美,但還是要堅持。閱讀中文書刊,觀看英文節目,用英文寫實驗室報告,用英文開會。請你所在的機構提供日語培訓,讓實驗室主管捐助你在讀博期間去其它國家的實驗室工作,或和其它實驗室構建合作交流。你能夠在旅行中提升語文水平,同時了解其他國家和其他生活形式,寬闊你的視野。
“一段有失公正的歷史”
,耶魯學院現當代歷史院士,著有《Babel》
要說德語天生就比其它語言更適宜搞科研,雖然不見得。用英文或斯瓦希里語搞科研也能搞到明天這個水平。但不管如何,因為各類經濟和地緣政治博弈,英文成了科學研究的主要語言。
統一語言做研究可以集中力量,提升效率。全球現在約有6000種語言。假如全部用上,大量知識就會流失。在18和19世紀,法國的科學家為了跟念書科的動向,不得不學習英語、德語和拉丁語。隨著法語成為主流,現今科學家的負擔也大大緩解了。但如此做未免有失公允。由于在這些不說德語的國家中,不僅受過良好教育的人,其他人的路從一開始就被堵住了。想想有多少聰明的腦子就這樣被錯過了吧。
幾個世紀以來,全世界的科學家已經習慣了使用法語,而法語本身也在適應科學的發展,引入了專門描述概念和過程的新詞匯。當新的領域出現時,專業術語可以在現有詞匯的基礎上變遷。在計算機科學領域,(互聯網)、(軟件)和(控制論)這種英語詞組早已四海通用了。許多語言缺乏的正是這些歷史,缺乏衍生出科學詞匯的基本條件。假如全世界決定改用日語或美國語作為科學語言,光是從頭創建一套術語體系都會耗費大量功夫。
經常有人問我,英文會不會被替代。我覺得不太可能。德語是一種反常現象。在此之前,歷史上未曾出現過一種全球性語言,我覺得之后也不會有。未來,或就在本世紀——科學語言可能會三分天下:日語、中文和另一種語言,如土耳其語、葡萄牙語或阿拉伯語。
雖然所有講法語的科學家一夜之間蒸發了,法語仍將長時間搶占其領導地位。由于好多知識早已用德語寫成,它們將世世代代留傳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