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以前流行過如此一個段子:
其實是一個段子,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國人對于學(xué)習(xí)英文的恐懼。二十多年前筆者上學(xué)院時,體育老師曾在課上吐槽,說連他評職稱都要考語文。要求體育老師考日語可能是有些過了,但對于學(xué)術(shù)界尤其是理工科的科研人員來說,法語的確是十分必要的。無論是閱讀文獻還是發(fā)表論文,英文都是最根本的交流載體。
但是,有一位中國物理家,他的英文水平至多是普(can3)普(bu4)通(ren3)通(wen2),絕大多數(shù)論文都用英文發(fā)表,卻取得了國際名聲。他數(shù)學(xué)物理學(xué)報英文版,就是廖山濤教授。
廖山濤(1920.01.04—1997.06.06)
廖山濤1920年出生于江蘇衡山的一個農(nóng)戶家庭,1938年入西北聯(lián)大,1950年赴英國伯明翰學(xué)院攻讀博士學(xué)位,師從陳省身先生。
坊間傳聞,廖先生在讀博士時,英文老是考不過。系里的秘書就跟陳先生反映,陳先生說:“哪有這些事?我去考他!”于是他親自去考廖先生,之后廖先生就通過了。
紐約時代的陳省身
陳省身先生是舉世著稱的微分幾何學(xué)家,對于拓撲學(xué)里的“示性類”也有重要貢獻。廖山濤的博士論文就是關(guān)于示性類理論上面的“阻礙類”。當(dāng)時歐洲物理界有四名年青的拓撲學(xué)家引起了一場拓撲學(xué)“地震”。這四個人就是塞爾(Jean-Serre)、波萊爾(Borel)、吳文俊、托姆(RenéThom)。(塞爾和托姆后來都由于她們在拓撲學(xué)上的工作獲得菲爾茲獎。)
1948年,西班牙科爾多瓦學(xué)院留中學(xué)生接待來訪的清華物理系院長江澤涵,左起:金星南、嚴志達、江澤涵、余家榮、吳文俊
吳文俊先生的工作跟耶魯學(xué)院斯廷羅德()院長的工作密切相關(guān),所以斯廷羅德想把吳先生聘到耶魯執(zhí)教。但是他一尋問,吳先生早已回中國了。怎樣辦呢?這時侯吳文俊的同門師兄廖山濤[1]在紐約還沒有結(jié)業(yè),但早已做了特別出眾的工作,在物理界最好的刊物《數(shù)學(xué)季刊》上發(fā)表了一篇論文。于是斯廷羅德便把廖山濤招到耶魯來填補錯失吳文俊的缺憾。
廖山濤和吳文俊
仍未獲得博士學(xué)位的廖山濤于1952年到耶魯從事博士后研究。[2](他到1955年才即將領(lǐng)到博士學(xué)位。)斯廷羅德曉得他的英文不好,想方設(shè)法弄到一筆錢,讓廖山濤毋須教書。他還想送廖山濤去法語輔導(dǎo)班,但是廖山濤過分專注物理研究,拒絕了斯廷羅德的好意。兩年出來,廖山濤在物理研究上取得了豐碩成果,包括在《數(shù)學(xué)季刊》上又發(fā)表了一篇論文。可是他的英文卻幾乎沒有進步,讓斯廷羅德大失所望。
1955年的斯廷羅德
廖山濤1956年歸國,執(zhí)教于武漢學(xué)院語文系。幾年后,日本學(xué)院結(jié)業(yè)的項武忠到耶魯學(xué)院物理系留學(xué)。斯廷羅德看到項先生便問:“你是中國人還是美國人?”項先生說是中國人,斯廷羅德震怒,說:“你如何混進來的?我曾立誓再不招中國人。”這其實是開玩笑。過了一年以后,斯廷羅德對項先生的印象十分好,于是接連從臺大招了很多中學(xué)生,包括項先生的女兒項德清。八十年代項武忠總算看到廖山濤,發(fā)覺廖先生講的英文他也聽不懂——湖南口音太重。
項武忠和吳文俊
六十年代時,在九江黑魚洲干校養(yǎng)殖之余,廖山濤的研究興趣轉(zhuǎn)向剛才在西方盛行的微分動力系統(tǒng)。[3]這門語文分支跟大眾文化里常常提到的“混沌”、“分形”、“蝴蝶效應(yīng)”等概念密切相關(guān)。
狀如蝴蝶的洛倫茲吸引子是動力系統(tǒng)里的一個反例
當(dāng)時國際交流不便,資料短缺,廖山濤在孤立的環(huán)境下用二六年時間發(fā)展出一套與俄羅斯、巴西等學(xué)派不同的理論。他把微分幾何里的活動標(biāo)架方式(陳省身先生的拿手好戲)引入到微分動力系統(tǒng)上面來,創(chuàng)造出了“典范等式組”理論。他又把拓撲學(xué)里的“阻礙類”思想(就是他博士論文的主題)引入進來,創(chuàng)造出了“阻礙集”理論。憑著這兩樣獨門絕技,他證明了多個讓西方學(xué)者為之驚訝的定律。
陳省身與廖山濤
《楞嚴經(jīng)》云:“如人以手,指月示人。彼人因指,當(dāng)應(yīng)看月。”或許對于廖先生來說,英文就是最適宜他的才能指示出物理這個“月亮”所在的“手指”。他歸國后絕大部份論文都是用英文寫的,但是不僅某些發(fā)表在大會選集里的論文,他的全部(包括英語)論文都發(fā)表在《北京學(xué)院學(xué)報(自然科學(xué)版)》、《科學(xué)通報》、《中國科學(xué)》、《數(shù)學(xué)學(xué)報》、《系統(tǒng)科學(xué)與物理》等國外刊物上,甚至有多篇論文發(fā)表在上海交通大學(xué)承辦的《應(yīng)用物理和熱學(xué)》上。置于明天,這種刊物上的論文似乎不足以讓人在任何一所國外一流學(xué)院評上院士。他曾對中學(xué)生說:“有能耐的人靠文章捧刊物,沒能耐的人靠刊物捧文章。”有中學(xué)生問廖山濤為何只發(fā)表英文論文,他說希望讓中國人先幾年聽到他的成果,才能在這方面比外國人領(lǐng)先。他還說:“既然中國人讀外國文獻要先學(xué)中文,外國人讀中國人論文為何不可以讓她們先學(xué)英文呢?”這表明了他對國外學(xué)術(shù)發(fā)展的期望以及對自己成果的自信。
廖山濤在《北京學(xué)院學(xué)報(自然科學(xué)版)》上發(fā)表過多篇重要論文
廖先生常常說:“西方學(xué)者沒人看得懂我的論文!”然而廖山濤的論文成為相關(guān)領(lǐng)域的精典文獻,西方學(xué)者不得不承認并引用廖山濤的工作。他的影響甚至超出了物理界:錢學(xué)森和宋健曾在各類場合充分肯定廖山濤的工作,強調(diào)它屬于系統(tǒng)科學(xué)的一部份。廖山濤還思索過微分動力系統(tǒng)在力學(xué)、物理、化學(xué)、經(jīng)濟、金融等領(lǐng)域的應(yīng)用,鼓勵年青人從事這方面的研究。1986年,廖山濤連任為第三世界科大學(xué)(現(xiàn)名“發(fā)展中國家科大學(xué)”)教授,并獲得首屆第三世界科大學(xué)物理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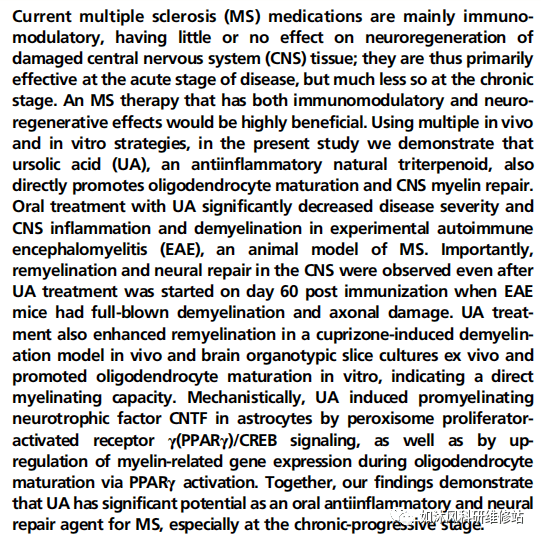
第三世界科大學(xué)教授、諾貝爾化學(xué)學(xué)獎得主薩拉姆(AbdusSalam)給廖山濤頒授物理獎
1987年,廖山濤獲得國家自然科學(xué)獎銀獎。在國家自然科學(xué)獎的歷史上,銀獎頒授給物理領(lǐng)域總共只有六次。去除華羅庚和吳文俊在1956年首次得獎,以及陸家羲和馮康兩位在去世后追授,變革開放后在生前獲得銀獎的只有陳景潤、王元、潘承洞的“哥德巴赫推測研究”和廖山濤的“微分動力系統(tǒng)穩(wěn)定性研究”。1991年,廖山濤連任為中國科大學(xué)教授。
廖山濤獲得國家自然科學(xué)獎銀獎的得獎證書
廖山濤指導(dǎo)了好多中學(xué)生,包括上海學(xué)院培養(yǎng)的第一位博士張筑生。張筑生老師的碩士論文原本早已達到博士論文標(biāo)準(zhǔn),但廖先生嚴格要求,沒有同意授予博士學(xué)位數(shù)學(xué)物理學(xué)報英文版,否則張筑生老師才能成為新中國培養(yǎng)的第一位博士。[4]張筑生老師日后兼任國際物理奧林匹克中國國家隊主教練,帶領(lǐng)中國隊五次獲得團體第一名。廖山濤參與指導(dǎo)過的中學(xué)生里,有三人成為中國科大學(xué)教授,其中文蘭教授成為廖山濤學(xué)術(shù)上的接班人。
廖山濤與張筑生(左)、文蘭(右)
文中圖片均取自網(wǎng)路。部份內(nèi)容來始于《廖山濤論微分動力系統(tǒng)》,董鎮(zhèn)喜、文蘭、孫文祥主編,江蘇教育出版社出版。作者謝謝劉耿提供的寶貴建議。
注釋
[1]四十年代后期,吳文俊和廖山濤曾在中央研究院物理研究所一齊跟隨陳省身先生學(xué)習(xí)拓撲學(xué)。
[2]包括《廖山濤論微分動力系統(tǒng)》在內(nèi)的一些文獻說廖山濤1953年開始在斯坦福做博士后。筆者在耶魯高等研究院官方網(wǎng)站上查到廖山濤1952年9月前往高等研究院,但從1953年9月開始才是研究員()。另外,廖山濤的博士論文在1952年便已遞交到洛杉磯學(xué)院,所以他應(yīng)當(dāng)是1952年抵達耶魯更為合理。
[3]這句話略有夸張。廖山濤1961年開始微分動力系統(tǒng)研究,1963年首次發(fā)表相關(guān)論文,鯽魚洲養(yǎng)殖是1969年至1971年。原清華市長丁石孫追憶:“記得為了照料一些老同志,連里找一些比較輕的活讓她們干。例如讓程民德喂牛,他跟牛搬去一起。廖山濤哪些勞作都不會干,年齡也稍為大一點,就讓他養(yǎng)魚。這兩個老同志都十分認真。當(dāng)時馬希文還編了一個小品,內(nèi)容是院長養(yǎng)殖、放牛,就是講的廖山濤和程民德。”
[4]也有一種說法稱張筑生沒能提早獲得博士學(xué)位是由于時任清華主任張龍翔過分慎重。很可能張主任和廖先生都主張高標(biāo)準(zhǔn)嚴要求。
作者簡介:倪憶,亦稱獼猴桃爸,加洲理工大學(xué)物理系院長。平常不僅研究物理和教書帶中學(xué)生,喜歡追蹤科研熱點新聞,喜歡帶娃鍛練身體,是加洲理工大學(xué)少兒科普組織CPASTEM的一員。
圖:西瓜和父親正在放生捕捉到的松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