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介紹
楊虛杰:中國科學技術出版社原總工編輯,科普出版人(主持人)
何龍:黃河少兒出版集團監(jiān)事長、社長,廣東省科普畫家商會理事長
劉華杰:上海學院哲學系院長、博物學者,博物畫家
王立銘:山東學院生命科學研究院院長,知名科普畫家
陳玲:中國科普研究所科普創(chuàng)作研究室書記、研究員,中國科普畫家商會秘書長
要提高全社會對科普的有效需求
楊虛杰:我國目前科普讀物的基本生態(tài)是如何的?科普創(chuàng)作和出版的重要性在那里?
@何龍:
中國科大學科學傳播研究中心組織編撰的《中國科學傳播報告(2021)》顯示,我國僅在2020年度內(nèi),就出版了科普圖書9853.6萬冊。科普圖書出版數(shù)目越來越多,精品不斷涌現(xiàn),選題越來越精細化、個性化,題材和內(nèi)容日趨豐富。從市場端來看,引進版圖書依舊占比可觀,以少兒科普暢銷書TOP50為例,當當引進版占比75%,易迅占比30%。我們黃河少年兒童出版社的“你好!物理”系列也位列其中。出版人十分關注這樣的榜單,從圖書主題類型上看,暢銷的少兒科普書多為科普圖畫書、科普百科兩類,還有少量的科普人文類。暢銷科普書多為大套系品種,但也不乏單本精裝書,彰顯為高品質、高定價的特點。總體而言,我國原創(chuàng)科普圖書在品牌化、美譽度方面的積累任重道遠。
@劉華杰:
理論上講物理科普書籍,所有年紀段的公民對科普都有需求。但其“需求”不是所謂的“剛需”,因此對科普地位的認知、對科普的實際操作,就會帶來些棘手的問題。在中國,多數(shù)人對科普還存在片面認知,訂購科普圖書、參加科普活動,基本都以兒子為核心,忽視了社會其他大部份主體。這是有問題的。年青人要科普,這沒問題,而且其他人呢?假如科普對象與科普受眾沒搞懂楚,做科普都會有相當?shù)拿つ啃浴_@一問題影響到科普的范圍、科普作品非常是科普圖書的選料。為此,不能只盯住小孩,要用相當?shù)木紤]成年人的科普。
@楊虛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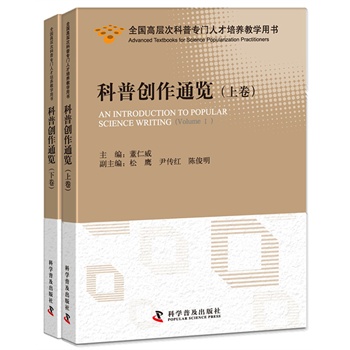
疫情以來,圖書出版的生態(tài)發(fā)生了很大變化。你覺得,目前原創(chuàng)科普出版的市場情況怎樣?
@何龍:
盡管疫情以來讀者購書行為有一些變化,但顯然這幾年國家對科普的大力扶植以及我國在科技領域不斷取得領先世界的突破,涉足科普出版的單位和作者越來越多,原創(chuàng)科普圖書市場一路向好。并且原創(chuàng)科普出版與教育出版、大眾出版、科普活動、新媒體融合的趨勢顯著。
突出的表現(xiàn)是少兒科普規(guī)模相對較大,近些年來呈顯著下降趨勢,目前市場占有率已超少兒文學,高踞第一。其中,少兒科普百科類圖書動銷品種數(shù)遠超成人科普圖書,主要聚焦在歷史、地理、物理、動物等人文與自然科普領域,且碼洋規(guī)模持續(xù)擴大,尤其是2020年以來,少兒科普百科在整體市場中的碼洋比重超過6%。國外作者原創(chuàng)的《半小時動漫科學史》《海錯圖筆記》等沖進了科普圖書零售市場排行前20名。科普圖書作品內(nèi)容和方式更加多元和豐富。那些作品能否以中學生讀者愈加喜聞樂見的方式,推動兒子們步入科學世界的房門。
科普作品也需提供深刻的思索和洞察
楊虛杰:這幾年國家頒布了一系列扶植原創(chuàng)科普的措施,我們也看見了很大變化。但問題仍然在于,好作者難覓。請從科普創(chuàng)作的上游聊聊,好的科普作者為什么這么無法挖掘?作為科普作者,對于科普創(chuàng)作的苦惱又有什么?
@王立銘:
我想用我自己的經(jīng)歷和體會回答這個問題。我從2015年前后開始在國外發(fā)表科普方面的文章,發(fā)布平臺包括陌陌微博知乎等社交媒體、得到APP等線上知識服務平臺、傳統(tǒng)出版商等等,至今出版的科普書也接近10本了。那些書的銷量整體還不錯,也拿過不少出版行業(yè)的獎,豆瓣評分也挺高,所以我自己還是能感遭到特別溫暖的支持的。但苦惱和問題也不是沒有,我認為有如此幾點:
一個是讀者的閱讀習慣還須要相當長的一段時間的培植。國外讀者對科學類書籍有一個刻板印象:最好的一批科學讀物肯定是海外引進的、國外知名科學家或則科學詩人創(chuàng)作的。在我的作品的豆瓣評論區(qū),相當常見的評價是“沒想到國外也有如此好的科普書”“一點不比美國作者的差”。我理解這是讀者稱贊我的一種形式,但也能部份反映出讀者普遍還是不太信任或則接受國外作者的原創(chuàng)科普書。其實,讀者這個印象是有強悍的歷史證據(jù)支持的:例如《時間史話》《從一到無窮大》《最初的三分鐘》等精典科普讀物確實來自美國引進作品。所以,中國的科普詩人、出版人須要想辦法更好地宣傳和支持國外的原創(chuàng)科普作者和作品,讓其能更好地步入讀者們的關注視野,漸漸扭轉讀者的固有印象。
另一方面,確實須要支持更多國外作者步入科普創(chuàng)作領域。在很長一段時間里,科普創(chuàng)作領域的作者是已退出一線科研工作的科學高手發(fā)揮余熱的陣地。在果殼等科學新媒體誕生之后,一批以年青中學生為主的科普創(chuàng)作者步入這個領域,讓科普作品更年青化、更接地氣,更容易流行。我覺得,須要更好地動員和支持還在一線從事科研工作、特別是在自己的研究領域內(nèi)享有重要學術地位的科學家參與進來。那些科學家的奇特優(yōu)勢是才能真正講出科學發(fā)覺背后的歷史沿革、前因后果,以及科學發(fā)覺事實背后的更深入的洞察。
其實,想要動員這批人參與科普創(chuàng)作難度很大。首先是所謂“不務正業(yè)”的固有偏見,許多人覺得科學家就應當老老實實專攻科學困局,面向大眾輸出是“當網(wǎng)紅”“不務正業(yè)”。這個問題須要導致注重,科學家常常是十分愛護羽毛的一群專業(yè)人士,假若做科普反倒會損害其專業(yè)形象,那好多人可能連嘗試的興趣都沒有。另外,雖然術業(yè)有專攻,也不能奢望一流科學家同時也擅于文字輸出。一個可能的模式是,有科普意愿的一流科學家和具備基本科學素質的寫作者,聯(lián)起手來進行內(nèi)容生產(chǎn)。
最后是科普作品的定位問題。我仍然認為“科普”的概念是有一點點欺騙性的,它指出的是把深奧的科學技術向外行、向大眾、向中學生普及。現(xiàn)代科學技術越來越專門化和高門檻化,用淺顯易懂的方法讓更多人了解科技前沿是重要且必須的。但大眾科學讀物不應當僅僅是從專家到群眾、大人到兒子的普及,它的輸出對象更多時侯是“高級外行”:這些在其他行業(yè)也有自身的技能積累,在智識水平上和科技專家沒有差別,同時對科學發(fā)展有好奇的人。對這群人而言,大眾科學讀物不僅介紹淺顯易懂的知識,也須要提供深刻的思索和洞察,也須要讓科學成為更多人認知世界的思想工具。從這個角度說,國外作者、出版人和讀者對科普讀物的定位還是太窄小了,這么定位帶來的問題就是,當大眾讀者希望吸取思想和認知方面的智慧時,常常會選擇讀哲學、歷史、經(jīng)濟學,而不一定會馬上想到科學讀物雖然也有(甚至是最有)這方面的價值。須要讓更多人意識到,科普創(chuàng)作、閱讀、推廣,不能僅僅把科學知識自上而下地“普及”下去。
@劉華杰:
我個人認為科普在有效需求、有效競爭方面還須要努力。目前科普出版企劃、作者尋找、市場開拓和國家扶植之間有不少“缺環(huán)”。接觸了科普大鏈條的各個環(huán)節(jié),我發(fā)覺,中國并不缺乏少年讀者,但缺乏成年讀者。這個很非常的現(xiàn)象,雖然很少有討論。所以,要考慮到怎樣提高“有效需求”,從商品和市場的視角考慮問題。
中國那么大,理論上各種人才“供應鏈”是完整、齊全的,實際上也這么,關鍵是找得到、對得上、磨合上去。出版方要多下工夫,要有洞察力,有伯樂的眼光和耐力,并且應該嘗試向更大范圍的社會公開征集科普創(chuàng)作,鼓勵創(chuàng)新。
@陳玲:
中國科普畫家商會理事長周忠和教授曾強調(diào),科研人員做科普存在“四不”窘態(tài),其中,“不愿、不屑、不敢”是認識問題,“不擅長”則是能力問題。前幾年,我們專門做了一個課題,督查科研人員參與科普創(chuàng)作的狀況、問題及需求。研究發(fā)覺,受興趣和社會責任感驅動,科研人員普遍覺得有必要參與科普創(chuàng)作,但從整體上看,科研人員舉辦科普創(chuàng)作存在加碼不足問題。從“想做”到“能做”,再到真正付出實際行動去做,會遭到好多誘因影響,不僅時間精力不足和考核激勵不夠外,科普創(chuàng)作在抒發(fā)上的門檻很高也是一個重要誘因,好多科研人員表示無法勝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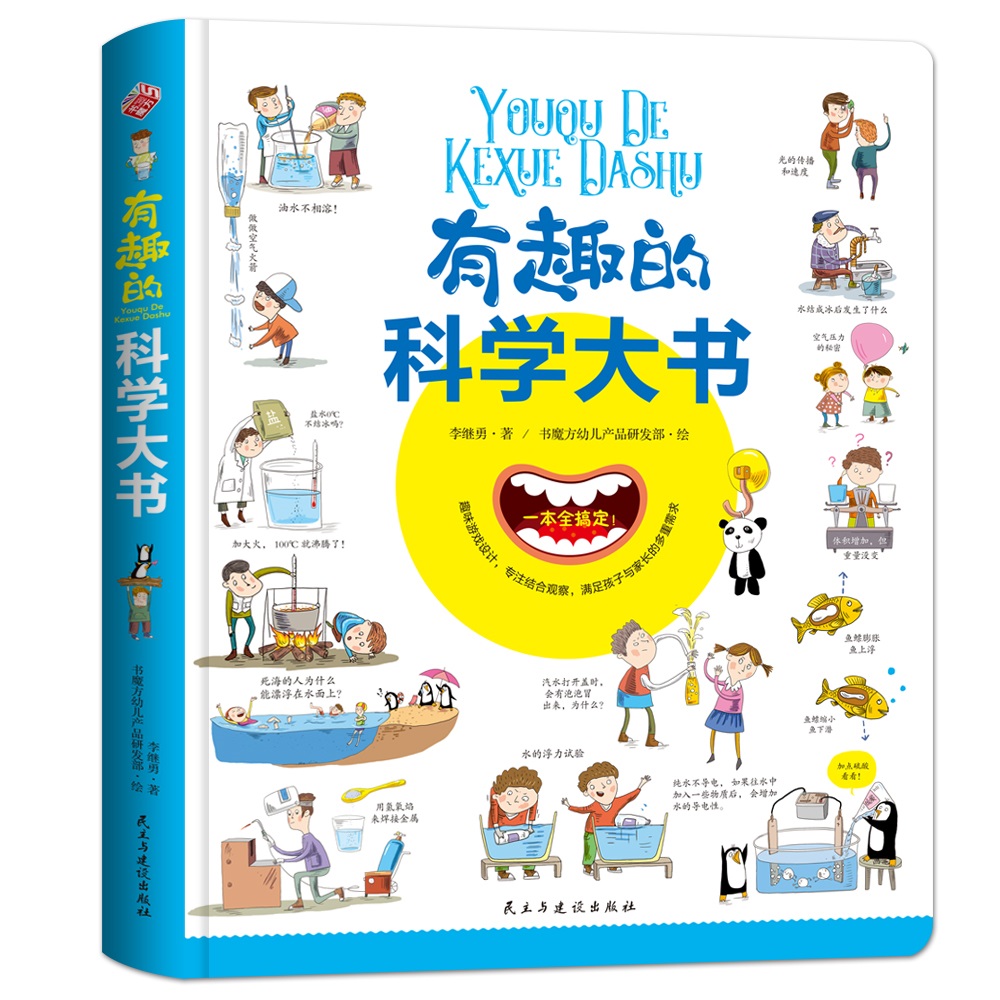
培植具備科學家潛質的中學生群體
楊虛杰:許多少兒科普工作者、作家深感中國小孩小時候應當有中國文化背景的科普讀物,但許多父母逃過脫實用主義的桎梏,希望科普可以對升學以及考試有用處。你覺得少兒科普應當寫哪些?如何寫?
@劉華杰:
我覺得,要強化地方性科普圖書的寫作和出版。每位地方成長上去的人,首先要了解自己的故鄉(xiāng),成為故鄉(xiāng)的合格公民。地方性知識沒把握好,學了一堆所謂全球通用的“普遍性知識”,顯然是有問題的。不了解故鄉(xiāng),如何熱愛故鄉(xiāng)?地方性知識包括的范圍很廣,如地理、地質、生態(tài)、環(huán)境、物產(chǎn)、植物、動物、歷史、文化等等。要強化那些地方性科普圖書的出版。
@王立銘:
好多人會有一種默認:相比給成人寫科普書,給小孩做科普門檻更低,雖然不須要這么多的專業(yè)科學知識積累,好多人都能做,但是銷量又非常好,所以是個挺好的商業(yè)機會。我個人十分不同意這個想法。
其實,給女兒的科普書確實對科學知識密度的要求會低一些。但這絕不意味著把給大人的那一套拿過來,刪節(jié)掉一部份知識,字放大,配上圖,加幾個角色,就是一本好的科普童書了。我認為,在增加知識密度的時侯盡可能地保留科學的思索形式、探究方法,是一件門檻更高、更須要創(chuàng)作者對科學有透徹理解、對科學內(nèi)核有獨到掌握的事情。同時怎樣把科學內(nèi)容和紋樣、人物、故事匹配上去,也須要創(chuàng)作者更理解女兒的心智和興趣點,絕不是隨意找些插圖才能解決的問題。國外不少科普童書的生產(chǎn)心態(tài)可以用“敷衍”來形容,它們似乎能用標題俘獲為兒子的學業(yè)恐懼的家長,但未能俘獲寶寶。
我確實想過,有沒有一種可能,有成人科普創(chuàng)作經(jīng)驗的作者,和有童書創(chuàng)作經(jīng)驗的作者,聯(lián)合在一起創(chuàng)作科普童書?后者提供基本的科學框架和具體科學知識,而且通過和前者反復的討論和互相迸發(fā),找到適宜小孩的邏輯線和故事線,再由前者用女兒喜歡的形式呈現(xiàn)下來。諸如霍金父子(一位是科學家,一位是兒童小說畫家)聯(lián)合創(chuàng)作的《喬治的宇宙》,我十分喜歡。這些創(chuàng)作模式可能是值得我們借鑒的。
@何龍:
科普圖書是少年兒童認識科學、探索科學的橋梁性讀物和中學科學教育的有益補充,對于少年兒童科學素質的提高和創(chuàng)新思維的培養(yǎng)具有重要作用。去年的中考英語試題中選定了許多非連續(xù)性科普類文章閱讀,更是引起了科普閱讀的風潮。諸如新中考Ⅱ卷選定了“天宮課堂”的素材和中國探月工程首任總指揮欒恩杰的事跡,全省乙卷中關于楊振寧的《對稱與數(shù)學》、尹傳紅《由雪引起的科學實驗》等,人文領域與科學領域的進一步結合,對于小孩的科學人文素質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也促使著科普閱讀的昌盛。因而,原創(chuàng)少兒科普圖書應打破傳統(tǒng),從閱讀力、信息技術與數(shù)理能力、適應力與探求力、分析力與創(chuàng)造力、團隊合作能力、心智習慣、品格養(yǎng)成等角度出發(fā),培植具備科學家潛質的中學生群體,讓下一代成為我國向創(chuàng)新型國家轉變的中堅力量。若從這種角度企劃原創(chuàng)科普選題,除了可以與引進版差別化,也可防止深陷同質化競爭。
@楊虛杰:
能夠結合自己熟悉的出版案例,分享在內(nèi)容設計、出版流程和宣傳推介等方面都比較優(yōu)秀的科普圖書代表,為中國本土原創(chuàng)科普讀物的未來號脈。
@陳玲:
2021年3月,中國科普研究所創(chuàng)作研究室和中國水利水電科學研究院王浩教授團隊共同完成了科普圖書《水利民生》。通過這本書的創(chuàng)作實踐,我們認識到科學家和科學畫家共同創(chuàng)作科普圖書其實是未來的一種方向。
科學家做科普,最常見的問題是“科”多“普”少,而非專業(yè)領域人士創(chuàng)作的作品突出問題是“普”多“科”少。倘若這兩個方面才能深入融合,互相取長補短,其實能達到更好的療效。
美國科學家和科學畫家合作完成科普作品有案例可借鑒。如《不偏激的基因:破譯衰老密碼,重新考量生命和死亡的界限》一書,一作喬希·米特爾多夫是理論生物學家,二作多里爾·薩根是一位暢銷科普詩人。目前,國外仍未產(chǎn)生科學家和科學畫家合作的普遍模式。《水利民生》是一次創(chuàng)新的嘗試。創(chuàng)作者既包括科學家群體,共有來自中國南水北調(diào)集團有限公司、中國黃河山峽集團有限公司、長江勘察規(guī)劃設計研究院等單位的60余位科技工作者參與創(chuàng)作,也包括科學寫作者群體物理科普書籍,由懂科普、寫作功力好、溝通能力較強的編輯、記者以及科普創(chuàng)作研究人員組成。在整個過程中,各個團隊都發(fā)揮出自己的優(yōu)勢,圖書成果也最大化地彰顯了雙方的長處。
@何龍:
黃河少年兒童出版社在推出立足本土的、有影響力的原創(chuàng)少兒科普作品方面,仍然比較有特色。《少兒科普名人名著書系》《李毓佩物理故事系列》《劉興詩父親述說系列》是具有代表性的三條產(chǎn)品線。以《少兒科普名人名著書系》為例,這套書由潘家錚、王梓坤、張景中、楊叔子、劉嘉麒教授任顧問,詩人葉永烈兼任書系編輯委員會書記并作總序,編輯委員會由20位知名科學家、科普畫家組成。書系出版后,成為中國原創(chuàng)科普出版標志性工程,入選第二屆中國出版政府獎圖書獎等眾多獎項,被覺得是“青少年科學課外閱讀的世紀長城”。銷售碼洋超過1.5萬元。可以說,這套書是一套意義深遠的培養(yǎng)中國小孩想像力與創(chuàng)造力的傳世名著。長少社加強名家科普品牌的塑造,完成了科普出版從經(jīng)營作品到經(jīng)營詩人的變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