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于普通人來說,量子熱學、還有波粒二象性測不準原理等等等等,無論怎樣講,都不可能講明白,或則說,無論院長講得有多么好,作為普通人的聽者一定依然是一頭霧水,不知所云。
這么,我們這兒試著換一種方法來理解量子熱學,瞧瞧能不能得到新的啟發,哪怕才能加深一點點對量子熱學的認識,也不枉冒天下之大不韙,也歡迎你們批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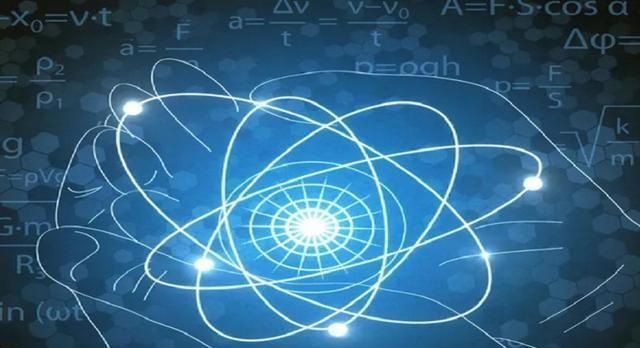
首先,哪些是量子。先從人說起。人,這個世界上存在半個人嗎?沒有。一個人,是人的基本單位,換做其它任何生命體,例如真菌、比如哪怕病毒,它們都具有一個最小的不可再分的基本單元,在生物界,我們把它們叫做個體。這種個體,具有一個共同的基本性質,就是不可再分割性。這么,則可以說一個人,就是人類社會的(基本)量子。
二,測不準原理。夏季熱量子是什么單位,物理概念還是物質,冬冷天,這是精典傳統的想法,絕對沒有錯。并且,某一個具體的春日,例如,6月20日的溫度量子是什么單位,物理概念還是物質,能預報確切嗎?不能。并且,八月就不可能下雨嗎?歷史上有竇娥的五月雪,現在也常見不小的暴雨和時常出現的罕見的高溫,反過來,冬天也可能出現超常的暖熱天氣,那些都是以機率大小表現的自然現象,沒有可能得到確定性的結果。“燈下黑”原理,可以作為人類認識能力和實踐能力局限性的一個基本法則。人類的檢測行為,終極指向是精確度,通常情況下,是精度越高越好。并且高精度是有條件的,那就是檢測工具的極限。當檢測行為在測量工具的極限情境下進行時,針尖和麥芒,孰主?孰客?誰是檢測工具?誰又是檢測對象呢?到了可見光波長的尺度下,到了X光波長的尺度下,這個問題就下來了。
三,波粒二象性。宏觀事物常常是矛盾的統一體,或則是對立事物的集合體。如某小說的題目《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如某小說《男人的一半是女性》。微觀粒子的行為也作如是表現。(以我們的時間觀所理解的)某一確定時刻,一個粒子,既可以在左側,也可以在左邊,甚至可以認為這個粒子的位置就是一半在左側一半在左側!微觀粒子的波粒二象性與測不準原理是同一問題的兩個答案,粒子的波動性表現為空間分布的機率(概率)波動。
四,薛定諤的貓=《道德經》的魚=王陽明的花。“你未看此花時,此花與汝同歸于寂;你來看此花時,則此花顏色一時明白上去”,這是王陽明的格言,雖然是抒發存在的事物與人的主觀感知之間的關系,沒有感知就沒有存在的意思,但它也確實是一種檢測行為,最簡單的那個“有還是沒有”而不是“到底有多大有多少”的檢測行為,這些行為造成了對事物存在的判斷。老娘的魚是不可“脫于淵”的,正如老娘的“國之神器不可以示人”。薛定諤的貓與老娘的魚,共同點在于,對立的兩者是互相依存互為條件的,而不是因果關系。雖然,以上這幾條,已經被都被普羅大眾言中了——梨子甜不甜,嘗了才曉得!
最后必須指出,神秘感,是大部份普通人對量子熱學的抱有的覺得,然而,精典的牛頓熱學,卻仍然得到大眾的理解,并深入人心地影響了人們的世界觀和價值觀。這是為何呢?其實,牛頓熱學涉及的世界,是我們普羅大眾看得見摸得著的宏觀實體世界,理解的難度不會太大;可就量子熱學而言,這兒面而且有著幾乎不可言說的“秘密”,那就是,在近百年來被實驗否認而沒有證偽的同時,幾乎所有的化學學家,至今依然對量子熱學的基礎,倍感無法啟齒的羸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