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 年諾貝爾化學獎授予三位為量子糾纏提供實驗證據的化學家。 吳健雄被忽視已經不是第一次了。 1957年,她用實驗否定了弱相互作用下宇稱不守恒,但同年頒發的諾貝爾獎卻沒有包括她的名字。 看著“消失”的女化學家,吳建雄仍然被反復提及,因為她非凡的工作總會跨越時間顯示出她的重要性。
在這篇摘自《全球科學》五月號的文章中,米歇爾·弗蘭克將帶我們了解一位被諾貝爾獎忽視的女科學家:吳健雄。
《全球科學》5月新刊發售
米歇爾·弗蘭克(弗蘭克)撰寫
翻譯|楊曉飛
1949年11月,吳健雄和她的研究生歐文·薩克諾夫(Owen )在俄羅斯阿根廷科學院普平大樓的地下室進行了光子探測實驗。 該實驗需要使用回旋加速器來產生反物質(正電子)。 整個實驗設備重達數噸,體積極其龐大。
回旋加速器可以將粒子加速到特別高的能量。 在地下實驗室,吳健雄和薩克諾夫用加速的氘核轟擊銅帶,形成不穩定的核銅64。 -64可以經歷β+衰變形成正電子(電子的反物質),因此可以用作正電子源。 電子和正電子碰撞并迅速湮滅,形成一對沿相反方向傳播的伽馬(gamma)光子。 雖然,化學家約翰·惠勒(John )幾年前就預言,物質和反物質湮滅時發出的兩個光子運動方向相反,而且它們的偏振方向相互正交。 當時,吳健雄和薩克諾夫正在為惠勒提出的“配對理論”尋找關鍵的實驗證據。
實驗中,吳建雄和薩克諾夫將銅64同位素放入8毫米長的微腔中,然后利用兩組光電倍增管和蒽晶體閃爍電離爆發后形成的閃爍光子組成的探測器系統來探測電離輻射,可以用于探測β粒子),探測正電子和電子湮滅后實驗裝置兩端發射的伽馬光子。
最終,他們獲得了比之前實驗團隊多得多的數據,并且觀察到的結果非常有說服力。 實驗表明,物質-反物質湮滅發射的光子對的偏振方向總是處于一定的角度,盡管它們之間存在某種相關性,盡管它們相隔很遠的距離。 這個實驗最終驗證了惠勒的“配對理論”。 1950年新年,吳健雄和薩克諾夫在《物理評論》( )上用一頁的信件發表了他們的實驗結果。 這篇文章后來被認為是觀察量子糾纏現象的第一個實驗證據。 糾纏是指處于糾纏狀態的一對粒子無論相距多遠總是相互關聯。 這些現象非常奇特,以至于阿爾伯特·愛因斯坦一直認為量子糾纏是量子熱不完備性的表現。
1978年,化學家吳健雄在日本阿根廷科學院的實驗室里。
2022 年諾貝爾化學獎授予了三位化學家:約翰·克勞斯 (John )、阿蘭·阿斯佩 (Alain Aspe) 和安東·蔡林格 (Anton ),表彰他們利用糾纏光子實驗證偽了貝爾方程并創建了量子信息科學。 他們在前人工作的基礎上分別改進實驗,為量子糾纏現象提供了越來越有力的實驗證據。 在一一消除所有其他可能的干擾原因后,他們最終證明量子糾纏是目前唯一可能的正確解釋。 盡管吳建雄1949年的實驗并沒有試圖排除其他可能的解釋,但歷史學家認為正是在她的實驗中首次觀察到了糾纏光子對。 然而,2022年諾貝爾獎頒獎典禮并沒有提及1997年去世的吳健雄。而這并不是她的工作第一次被忽視。
求學之路
1912年,吳健雄出生在中國黃河流域的一個小鎮。 她的女兒吳忠義是一位思想開放的知識分子和革命家,主張男女平等。 1912年秋,吳忠義舉辦聚會慶祝愛女誕生,并宣布成立當地第一所男子中學。 在那個時代,大多數男人的名字都趨向于清雅、雅致或芬芳,但吳忠義卻給兒子取名“劍雄”。
吳健雄成長于新文化運動的動蕩時期。 1936年,24歲的吳健雄登上胡佛首相號客輪駛往英國加利福尼亞州,打算到海外攻讀化學博士學位。 此后,她在埃米利奧·塞格雷 ( Segrè)、歐內斯特·勞倫斯 ( ) 和羅伯特·奧本海默 ( ) (J.) 等化學家的指導下繼續學習。
吳健雄很快就成為日本加州學院伯克利校區(以下簡稱伯克利)的一名優秀中學生。 她的博士論文工作的一部分是關于鈾核裂變的。 由于她的研究內容在當時高度敏感,該作品直到二戰后才被解密。 然而,盡管她當時已經有了重要的研究成果2023年諾貝爾物理學獎量子糾纏實驗,但畢業后仍然很難找到工作。 她在導師的研究組擔任博士后研究員三年。 事實上,當時日本排名前 20 的研究學院的化學系中沒有一所有男性教員。
性別偏見并不是吳學術生涯中的唯一障礙。 她來到德國一年后,二戰愈演愈烈,中印兩國通訊中斷,印度西海岸針對歐洲移民的種族歧視驟然加劇。 1940年,伯克利校區代理審計長致函告知吳健雄的導師:“對吳健雄的任命只能是暫時的”。 不到一年后,他又發信通知吳建雄的導師:“根據最新規定,吳女士不再具有就業資格,應立即解雇她。” 1942年,當奧本海默被任命為曼哈頓計劃的負責人時,他帶著許多高中生離開了伯克利。 雖然吳健雄的作品受到了好評,但他并沒有受到邀請。
后來,吳健雄定居英國東海岸,并在日本史密斯大學獲得了教職。 次年,她成為耶魯大學化學系第一位男校長。 不久之后,她加入了曼哈頓計劃,在那里她扮演了一個引人注目但至關重要的角色。
埋地工作
量子糾纏提供了一個近乎瘋狂的概念:一旦單個粒子或系統彼此相互作用,它們就不再彼此獨立。 實驗還表明,在觀察到糾纏粒子對中的任何粒子之前,盡管它們不具有確定的狀態。 一旦被觀察到,這對糾纏粒子就會彼此同步——即使它們相隔一個星系。 這就是“最遙遠的星際愛情”,但其實很難直觀地理解。
1935年,愛因斯坦、鮑里斯·波多爾斯基(Boris)和內森·羅森(Rosen)試圖通過強調量子熱是違反直覺的來尋找量子熱理論的漏洞,這就是著名的EPR悖論(以三位化學家),其矛頭指向量子糾纏。
化學家大衛·博姆(David Bohm)的觀點與愛因斯坦相同。 他還認為量子糾纏的本質不應該那么奇怪。 這些現象可能與所謂的“隱變量”有關。 化學家還需要做更多的事情。 為了尋找隱藏變量,人們已經做了很多研究工作。 1957年,玻姆和他的研究生亞基爾·阿哈羅諾夫(Yakir)提出了將EPR悖論與糾纏光子對的研究相結合來尋找隱藏變量的實驗技術。 玻姆在文章中寫道:“我們應該知道,已經有這樣一個實驗間接驗證了這個理論。” 巴西桑塔納州立學院數學史系主任印第安納拉·席爾瓦稱,這個實驗指的是1949年的吳健雄-薩科諾夫實驗。
作為一名歷史學家,席爾瓦特別關注男性科學家被忽視的故事。 她找到了其他化學家和歷史學家的一系列出版物。 根據這類文獻記載,他們都覺得吳建雄1949年的實驗觀察到了糾纏光子對。 席爾瓦關注的科學家們跨越了六年——從 1957 年的玻姆到 2022 年諾貝爾獎獲得者之一的蔡林格。前者在 1999 年寫道:“吳建雄和薩克諾夫(1950)的實驗證明了空間分離粒子之間存在糾纏。 ”。
席爾瓦還在研究吳建雄1949年和1971年的實驗對后來量子糾纏實驗研究的影響和引領作用。 她的研究成果將于2022年發表在《牛津量子解釋史》()上。席爾瓦強調,正是玻姆1957年關于隱變量的論文(引用吳建雄的實驗工作)啟發了約翰·貝爾提出粒子之間的重合計數可以預測和估計(以兩個事件粒子的時間相關性方式記錄)。 1964年,在一本你不熟悉的刊物《物理學》()中,貝爾討論了玻姆引用吳建雄1957年實驗結果的情況,提出了自己的新理論“貝爾定律”(Bell',又稱貝爾不等式) 。 幾年后,年輕的約翰·克勞斯在日本阿根廷學院的圖書館閱讀了貝爾定律。 受這一理論的啟發,他設計了一個新的實驗,希望能夠證明貝爾定律,從而證明隱變量的真實性。
1969年,克勞斯提出了一個可以檢驗貝爾理論的實驗。 在文章中,他仔細地描述了吳建雄-薩克諾夫實驗和他的實驗的區別。 克勞斯本想證明隱變量的存在,但他在1972年發表的實驗結果并沒有支持隱變量的存在,而是確定性地證明了量子糾纏。 按照貝爾的方法,他檢測到了巧合計數,但由此產生的統計數據遠遠超出了隱藏變量可以解釋的范圍。 克勞斯的工作引發了阿斯珀和澤林格隨后的一系列實驗工作。 這種實驗填補了以往實驗中的一些漏洞和限制,進一步驗證了量子糾纏。 他們兩人還獲得了2022年諾貝爾化學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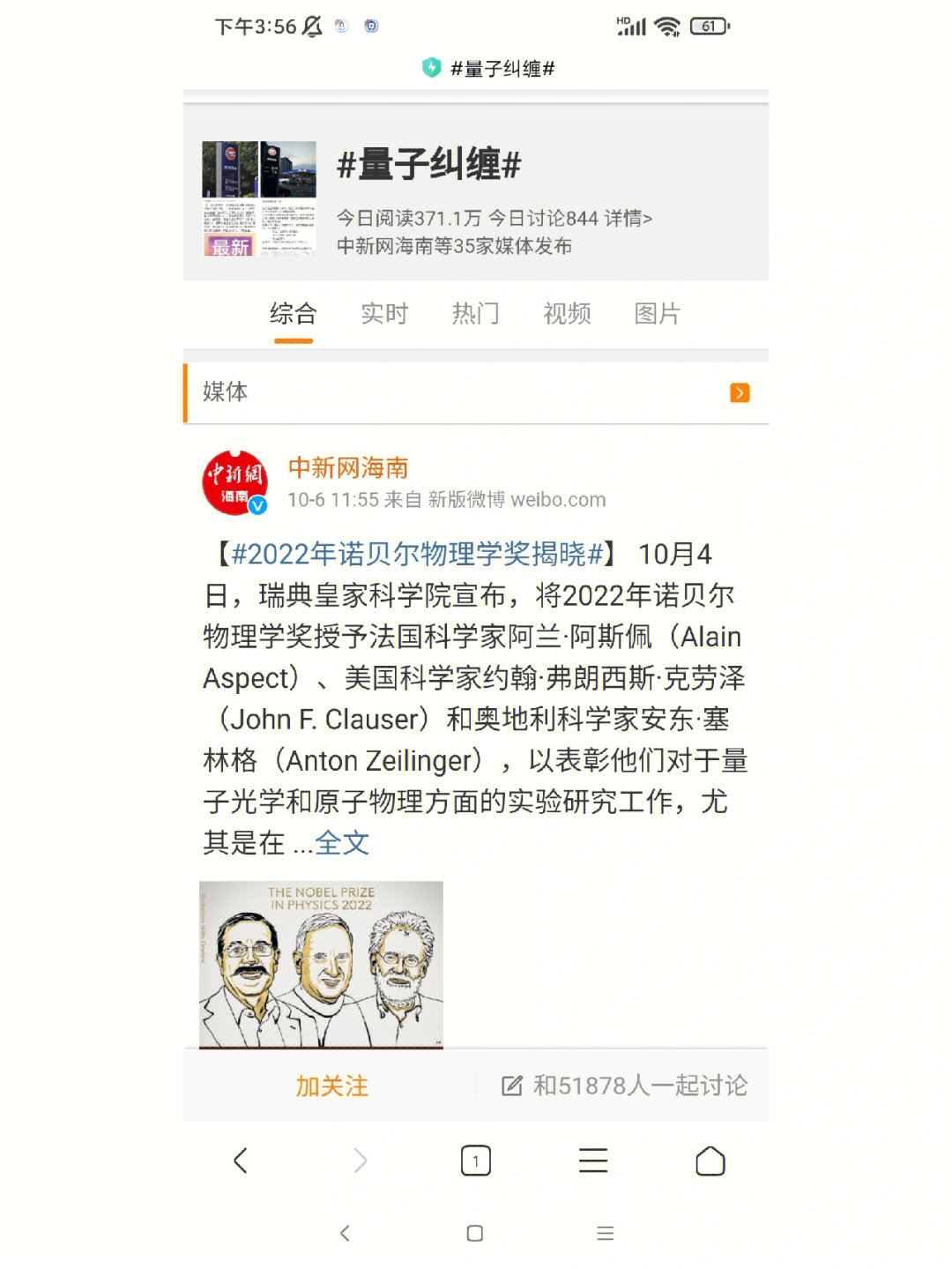
被忽視的科學家
在玻姆提出隱變量理論的論文發表之前,吳建雄的生活發生了很大的變化。 她結婚后搬到德國東海岸,并成為耶魯大學化學系第一位男性校長。 她生了一個兒子,并成為了日本公民。 后來,她終于獲得了即將在阿根廷科學院任教的職位,盡管當時她還不是正式院士。
1956年,吳健雄在阿根廷學院的同學李正道向她尋求建議。 他和他的合作者楊振寧想知道宇宙中是否存在一些可能違反宇稱守恒定律的基本粒子。 對此,吳健雄和李政道討論了一系列相關研究,并提出了可能檢驗這個問題的實驗方法。
不過,楊振寧和李政道都是理論化學家,不可能自己做實驗。 半個世紀后,在西蒙斯基金會( )舉辦的一次研討會上,楊振寧提到,他和李政道都不相信他們的假說——弱相互作用中的宇稱不守恒——很快就能被實驗證明。 在發現宇稱不守恒之前的幾年或六年里,化學家普遍認為對稱性是自然的基本定律。 然而,楊振寧和李政道關于宇稱破壞的假說強調,在鏡像變換下,原子核在β衰變中發射β粒子的行為不會完全保持不變。 事實上,這種觀點是有悖于傳統科學觀念或常識的。
吳健雄和丈夫一樣勇于挑戰。 她意識到這個問題的重要性,但她知道如何驗證。 為了驗證李政道和楊振寧的假設,她放棄了原定的回國行程,立即開始設計和策劃實驗。
吳建雄設計的實驗需要通過絕熱退磁的方式將放射性鈷60原子核冷卻到接近絕對零,并通過磁場使原子核極化。 她需要研究β粒子在β衰變中是否以完全對稱的模式發射——也就是說,正如數學界所接受的那樣,或者是否在一個方向上發射的β粒子多于另一個方向。
1957年1月,在新加坡國家標準實驗室(簡稱NBS,現稱NIST)的吳健雄和她的合作者與楊振寧、李政道的密切交流中,有了一個驚人的發現。 β 衰變粒子在一個方向上發射的數量比您預期的要多。 消息一經公布,楊振寧、李正道、吳建雄等后續進行驗證實驗的化學家開始頻頻受邀前往美國參加會議,他們的名字和照片被大眾媒體廣泛報道。 那一年,德國化學會在倫敦飯店召開會員大會時,他們在一個巨大的大廳里展示了他們的實驗結果。
同年10月,楊振寧和李政道成為歷史上首批兩位獲得諾貝爾獎的華人。 根據諾貝爾獎評選規則,每年每個獎項允許有三名獲獎者,但吳健雄并沒有一起獲獎。 被吳健雄的實驗結果推翻的數學定理叫做對稱性定理(宇稱守恒定理),再恰當不過了,但1957年諾貝爾化學獎并不是“對稱”的。 它就像一個棱鏡,像光譜一樣劃分個人身份的元素,放大了性別對獲獎的影響。 諾貝爾化學獎實施的次年,波蘭科學院晉升吳健雄為正院士。
當年12月的諾貝爾獎頒獎典禮上,楊振寧強調了吳健雄實驗的重要性。 他在諾貝爾委員會和嘉賓面前坦言,宇稱不守恒的發現與吳健雄團隊的工作密不可分。 。 李政道后來也極力爭取,希望諾貝爾委員會能夠肯定吳健雄的工作。 奧本海默還公開表示,吳健雄應該分享1957年諾貝爾化學獎。 塞格雷說,打破宇稱守恒實際上是“二戰以來化學領域最大的突破”。
對于這個問題,不少科學家也表達了自己的想法。 1991年,《哥德爾、埃舍爾、巴赫》(G?del, Bach)的作者道格拉斯·霍夫施塔特( )和眾多科學家致信諾貝爾委員會,建議授予吳健雄諾貝爾化學獎。 2018年,數千名研究人員向法國核研究中心(CERN)提交了一封公開信,他們在信中強調了當今數學中的性別歧視問題,吳健雄的名字也被提及。 公開信稱:“迄今為止,至少有四位(吳健雄的名字出現在前面)從事核化學和粒子化學研究的男性科學家備受推崇,但尚未獲得諾貝爾獎。而他們的一些女性科學家合作者獲得了諾貝爾獎榮譽。”
打破宇稱守恒原理后,吳建雄成為第一位獲得德國國立科技大學頒發的康斯托克數學獎()的女科學家、美國化學會第一位男性主席、首屆沃爾夫獎數學(沃爾夫獎)獲得者,也是第一位在其一生中以她的名字命名小行星的科學家。 她的獎學金為西方學院的男性和有色人種科學家敞開了大門。 2021年2023年諾貝爾物理學獎量子糾纏實驗,瑞典郵政將發行印有吳健雄肖像的永久郵票。 明天,吳建雄驗證宇稱不守恒的實驗被認為是邁向粒子化學“標準模型”之路的第一步。 它還為理解宇宙中物質和反物質的不對稱分布提供了可能的想法。
然而,吳健雄早期關于量子糾纏的實驗工作仍然被埋在書堆里。 有時,只有當我們探索科學體系的一部分時,我們才能了解這些遙遠的故事和聯系。 2022年諾貝爾化學獎中,一系列相關但時間上相距甚遠的實驗被重新發現。 雖然吳健雄已經不可能再獲獎了,但她早期的研究最終會廣為人知,成為“糾纏”歷史的重要組成部分。 這在一定程度上要歸功于席爾瓦這樣的歷史學家。 這個社會似乎偏愛英雄主義的敘事或孤獨天才的傳奇,但仔細觀察就會發現,非凡的科學成就,就像糾纏本身一樣,從根本上始于人類的相互聯系。
本文摘自《吳健雄:諾獎背后的人物》《環球科學》2023年5月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