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乃人生大事。喪事,百度說是活人對(duì)死人的揮別典禮。
繼1985年殯葬變革開始,火葬這一中華傳統(tǒng)喪葬典禮正逐漸被火化代替。除了是政治上的要求,近年全省人口急速下降、城鎮(zhèn)化進(jìn)程加速、新冠疫情阻隔等都成為下葬典禮衰落的重要誘因。
作為出生于21世紀(jì)的年青人,我的老家——冀北農(nóng)村,目前算全省少數(shù)仍保留著這一古早典禮的地方。上個(gè)月時(shí)逢父親逝世,我便從頭到尾出席了一場(chǎng)幾乎被時(shí)代吞滅的喪事。
我想記錄那些,絕非要拿它與現(xiàn)代喪葬典禮做比較。雖然火葬典禮中盡是些沒有來源的“規(guī)矩”,但作為中華傳統(tǒng)喪葬典禮,存在過,便是記錄它最好的理由。
以下是我對(duì)母親喪事的追憶,其中包含了一些個(gè)人情感。這是作為傷者家屬、同時(shí)也作為農(nóng)村戶口的我而言,對(duì)這片農(nóng)地飽有的無法回避的愛情。
一、離世
乙未年三月廿三18時(shí)21分,母親在母親、四伯的凝視中咽下最后一口氣。十分鐘前,你們還聚在旁邊談?wù)撃赣H能夠喝下水,精神狀態(tài)不錯(cuò)。可這一次,父親進(jìn)去再看父親,下來時(shí)已紅了眼窩。
母親在養(yǎng)老院逝世,她的三個(gè)孩子都在外省工作,這幾日聽聞父親病況加重她們輪流回去探視。四伯是最后一個(gè)回去的,父親也是在見他那天決定撒手人寰。母親說:“做媽媽的在臨終前也得見過所有孫輩能夠放心啊。”
四伯叫來救護(hù)車把母親運(yùn)回去,大人們上了救護(hù)車,我坐姐姐姐夫的車跟在前面。
回母親家的路上我們穿過一片片農(nóng)田,搖下車窗,夏季的風(fēng)卷起一層層沙,一望無際的小麥地里看不到忙作的農(nóng)戶,遠(yuǎn)處的山在晚霞的襯托下輪廓漸漸清晰,一大一小兩輛車在道路上行駛著,載著父親的靈魂回去。
姐姐的車載電臺(tái)此次總算沒放網(wǎng)紅迪斯科,而是吳青峰演唱的《起風(fēng)了》。窗前的風(fēng)吹的我睜不開眼,更有幾滴淚沿著口罩流下。我,在傷心嗎?
我與父親交情并不很深,讓我追憶母親,雖然只有每年向她拜年時(shí)她回應(yīng)我的一聲“慧慧啊”。
這時(shí)耳畔響起“晚風(fēng)吹來你鬢間的白發(fā),抹去追憶留下的疤”。我突然明白了為何會(huì)掉下淚滴,原先看著母親從黑發(fā)到白發(fā)的是父親,我擔(dān)心父親喪失了借助。
從那天起,父親再也沒有了爺爺奶奶。
二、入殮
逝者要換喪服,從貼身衣服到衣服外套都需換新。即使是夏季,人這一生要穿的所有衣物都不能少。規(guī)矩說,這樣傷者能夠體面地離開。
為父親換上衣的環(huán)節(jié)我沒有出席,只是在家旁邊等著。四六年沒來過這兒,母親家旁邊長(zhǎng)滿了雜草,鐵門也生了銹,門外那用地磚制成的巨大春聯(lián)也漸漸褪了色。
(兒時(shí)就在父親家旁邊的春聯(lián))
過去一年姐姐都在養(yǎng)老院生活,庭院里的一塊地被叔父借去種滿了獼猴桃和豇豆。這個(gè)時(shí)節(jié),種子剛好結(jié)了些果實(shí),但主人去世,這種剛才成形、還是白色的圓滾滾的櫻桃只能被鋸掉。我看著一摞被扔到外邊的翠紅色菜秧,為它的命運(yùn)慨嘆。
(被丟棄的櫻桃)
母親家庭院里有三間房,一進(jìn)門的那間我從來沒進(jìn)去過,直至那天我才明白為什么。原先在二六年前,身為石匠的父親就給自己和母親做好了棺木,那間房里放置的全部是二老死后須要的用具。這兩個(gè)老太,連后事都早早打算好了。
下葬之前,大人們找來附近幾個(gè)村最有名的陰陽(yáng)(也可以叫風(fēng)水大師),幾時(shí)幾刻下葬、家中怎么布置都由陰陽(yáng)說了算。我只記得那位大師讓媽媽把庭院里一處沒完全堵住的墻填上,說這樣不會(huì)破財(cái);還有在家中六個(gè)位置用板磚擋住哪些東西,我也不知道哪些理由。
大人們打算妥當(dāng),白天九點(diǎn),母親的五個(gè)兒女全部見過逝者,父親被幾個(gè)人抬著入了棺。
鐵釘釘下的那刻,父親的面容便不在這世上了。
三、儀式打算
從下葬到安葬,聽說棺木前的香火不能斷,所以父親和爺爺四伯輪流守靈,大概共計(jì)三十五小時(shí)。期間,忙家人開始打算開吊和下葬典禮須要的東西。
在喪葬禮俗中,開吊是喪家接受親友拜祭的日子。在農(nóng)村,開吊的場(chǎng)所通常選在自家庭院,所以父親離世昨晚,忙家人便開始在庭院里搭起了靈棚。所謂忙家人,是屋內(nèi)辦席附近民居里來幫忙的人。
搭靈棚并不怎樣費(fèi)事,找來幾根長(zhǎng)竹簽,用鐵絲將其互相捆綁,外邊用幾個(gè)某品牌肥料的包裝袋蓋上。這么一來,一個(gè)防小風(fēng)陣雨的靈棚便搭好了。父親的棺木在靈棚最上面,向外依次擺放一個(gè)小木桌,一蒙自鐵盆,外邊則鋪了一層被子。
擺貢品用的這個(gè)小木桌打我出生起母親就在用。平日里它總被置于炕上,父親母親喝水、縫衣物、放水杯都須要它。此次再會(huì),小木桌的桌面和桌腿交界處早已被不同的廣告紙和膠水纏繞了好幾圈,桌腿也顯而易見地光滑了許多,帶上了時(shí)光賦于它的蒼涼。幾年前父親的喪禮也全程都在用這張木桌,近三六年的歲月,木桌也算完成了它對(duì)兩位奶奶最后的使命。
接出來披麻守孝。村里的兩個(gè)裁縫,將一塊粗棉布剪幾刀、不用任何縫制,便做好了一件孝衣。孝衣是像外套一樣的衣服,披在頭上,把線繩系在腰部,在夏季還算涼快。孝帽則主要拿來區(qū)分家中不同地位。爺爺是家里長(zhǎng)子,他和二伯父頭戴倒船型的圍巾,圍巾后還有一片長(zhǎng)長(zhǎng)的麻到腰部,四伯和我爸則沒有。侄子侄女輩頭戴方形棉布帽,男性的圍巾左側(cè)繡有一個(gè)紅絨球。
(我穿戴孝衣)
最后便是通知親朋出席喪禮。這件事全程由叔父操辦,由于他是大女兒。爺爺給你們打電話時(shí)我在后面,聽他用土語(yǔ)和電話旁邊一遍遍說“我娘摔倒了,今天下午來吧。”期間遇見一位反詰摔倒是哪些意思,爺爺很小聲講“那我換句話說,我娘死了。”
原先一個(gè)人的“跌倒”也可以是一個(gè)人的逝世。
四、開吊
遺體在靈棚里放置十天后,第一天,總算到了開吊的日子。
我六點(diǎn)半到爺爺家旁邊,不僅幫大人跑腿買東西,其他時(shí)間就坐在旁邊的土堆上看景色、看行人。母親家是村口的第一家,但凡進(jìn)村基本都要經(jīng)過這兒。說是在看行人,可在這個(gè)只剩不到一半業(yè)主生活的村莊里,我能看到的行人基本都是出席父親喪事的同事同學(xué)。也正是這三天,我看到了好多今生可能只碰面一次的奶奶、姑姑們。
這種親朋大多結(jié)伴而至,不認(rèn)識(shí)的表姑們毛發(fā)大多斑白,他們四肢雖然也有些不便,你們互相攙扶,平緩走到家旁邊。我和爸爸躺下迎接,互相打過招呼,親朋便進(jìn)屋給總管份子錢,喪家通常還禮一盒煙。按規(guī)矩,喪事隨份子要在喪禮之前,也就是遺體停放兩天內(nèi)。所以你們通常在隨禮后開始嘮家常。
(我坐在旁邊土堆前傻笑)
人基本到齊,開吊打算開始。父親的棺木左右前方跪著主家人,右邊是三個(gè)孩子,右側(cè)是三個(gè)媳婦。按規(guī)矩,兩個(gè)兒子娶親后便不算主家人,所以大姑和三姑并沒有席位。第一支香由最年長(zhǎng)的爺爺點(diǎn)起,這時(shí)開吊典禮便算即將開始了。
在主家人給傷者做完祭祀典禮后,葬禮的總管便站在靈棚旁一批批的喊人們進(jìn)去給母親點(diǎn)香、磕頭、燒紙。進(jìn)去的次序也很有講求,先是親朋、女兒岳父、孫子、外孫,最后才是我們女兒輩。
到我進(jìn)去祭祀,總管遞給我三支已燒毀一半的香,其中有一截不留神掉落燙到了手臂。我走到靈棚里三鞠躬是給死人祭拜嗎,按父母的指示右手呈叩頭狀拿香,對(duì)著父親棺木前的相片三作揖,之后將香插入快要插滿的小香爐中。接出來便跪在地上,就是之前種著小櫻桃的那片地。雖然鋪了一層毛毯,我也能清晰地感遭到泥土的厚實(shí)。按規(guī)矩,我要給媽媽磕三個(gè)頭,算上幾年前出席父親喪事,這還是我第二次叩頭。可能有些緊張,全程我都在想“帽子會(huì)不會(huì)掉下、會(huì)不會(huì)不合規(guī)矩”……后來,禮帽果真掉在了地上,我在磕完最后一個(gè)后迅速拾起戴在身上。
到了最后一個(gè)環(huán)節(jié)——燒紙。木桌前的鐵盆派上了用場(chǎng),這兒的火仍然很旺,桌上的香也在卯足了勁的燒。整個(gè)靈棚瞬間“烏煙瘴氣”,熏的我不自覺留下淚水。我和哥哥接過我爸遞過的香燭,一次三五張得掉進(jìn)紙盆。父親讓我們喊媽媽拿錢,我不會(huì)講土語(yǔ),便用普通話一字一字的喊著“奶奶,付錢。”據(jù)說,喊逝者付錢才能讓她在天之靈盡早收到。
鐵盆里的灰燼在夏風(fēng)的映襯下蠢蠢欲動(dòng),看著紙灰飄上天空,身后的弟弟說道:“奶奶早已收到了啊。”
五、出殯
開吊第二日是喪禮,也是整個(gè)喪事中典禮最重要的三天。母親這一輩推行火葬,下葬便意味著將父親的棺木從家抬到后山的墓園安葬。
按規(guī)矩,送葬的過程中做兒子的不能抬頭。我不曉得理由,問大人,她們也不曉得。為了追隨行進(jìn)路線,我只能右手拉著老婆系在孝衣背部的線繩,由上面的人一個(gè)推動(dòng)一個(gè)向前搬動(dòng)。我的耳朵全程盯住手掌那雙早已堆滿黃泥的鞋子,身體不由自主地從父親家旁邊搬到了村里的小路。
這時(shí),妹妹們和弟媳們開始大喊。一聲聲“娘啊,娘啊”此起彼伏,仔細(xì)聽倒也能聽出其中的節(jié)奏感。以四四拍為基準(zhǔn),“娘”發(fā)四聲,占一拍;“啊”發(fā)一聲或小聲,長(zhǎng)音三拍。其中,屬大姑的聲音最有識(shí)別度,她能精準(zhǔn)地把尾音托長(zhǎng)布滿一小節(jié)。在大姑的率領(lǐng)下,三姑、大伯父、二伯母也開始嚎啕抽泣上去,你們用復(fù)調(diào)推動(dòng)的感傷與想念成為此次喪禮過程中十分具代表性的一環(huán)。
其實(shí)為襯托親戚們的哭聲、又似乎為了更惹人注目,忙家人開始把一大早置于街邊的一串串紅爆竹點(diǎn)著,與二踢腳一起,和哭聲互相輝映。若是條件準(zhǔn)許,這時(shí)中國(guó)傳統(tǒng)殯葬鋼琴二胡應(yīng)當(dāng)出場(chǎng)將這或喜或悲的氣氛襯托到極至。
不過在三天前,鄉(xiāng)里代表找到我爹,明令嚴(yán)禁使用鼓號(hào)隊(duì)。和這些說不上名的風(fēng)俗一樣,沒有理由。
點(diǎn)了一路的鞭炮,眼前一片灰霧,其中參雜著些許炸開的黑色包裝紙和燒成灰燼的香燭。我的眼前煙霧繚繞,由于騰不開手,耳朵被熏得只得重復(fù)用力閉眼再掙開的動(dòng)作,企圖借此減緩眼痛。
(喪禮的那條街)
在這樣的氣氛下,我有些許歉意。我問身邊小我一歲的弟弟:“我們不哭會(huì)不會(huì)不太合適。”她回我:“不哭也好過假哭”。
我不曉得哪些是真哭哪些是假哭,但哭聲越嘶聲裂肺,旁人總歸會(huì)認(rèn)為我們一家是孝敬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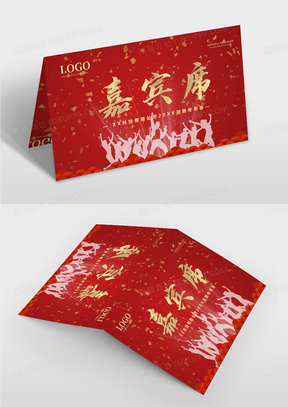
六、吃席
后面的幾項(xiàng)活動(dòng)基本都圍繞傷者轉(zhuǎn),吃席則是專給活人辦的。
自古中國(guó)人吃席無非是紅白兩種,離婚婚嫁是喜事,你們叫來親朋一齊見證一對(duì)新人開啟新的家庭;去世是喪事,你們圍坐一起悼念故人、珍視與故人的情義。無論紅事還是喪事,都能借此為抓手讓多年不聯(lián)系的親朋好友再度聚在一起,讓那些有血緣關(guān)系的情義再次相連。
之前農(nóng)村吃席大多請(qǐng)廚子來家里,但這種年隨著農(nóng)村旅店行業(yè)日漸發(fā)達(dá),去餐廳吃席似乎更為省事。我們此次在對(duì)門村旁邊找到一家才能容納9桌顧客的餐廳,一桌點(diǎn)了11個(gè)菜。由于按規(guī)矩,辦喪事注重湊單,無論是吃的飯菜、擺的祭品或是隨的禮都是雙數(shù)為佳。
我很喜歡吃席這個(gè)環(huán)節(jié)。不僅作為小孩才能一下吃到更多菜肴,最令我沮喪的是一家人不管之前多少矛盾都能在此刻化解。由于在“死者為大”這句話前,其他哪些問題都不值一提。
父親逝世后,父親的五個(gè)兒子們因一些問題形成矛盾,平日里不再來往,春節(jié)也只是為盡孝行和母親一起生活。此次你們聚在一起吃席,父親和他的弟弟妹妹們總算可以再像一家人一樣坐在一起嘮家常,她們母女五個(gè)也遇見了好多兒時(shí)的玩伴,你們?cè)陲堊郎嫌姓f有笑,追憶童年軼事。提及母親去世時(shí),你們沉默片刻,而后幸好父親83歲高壽離開,沒有經(jīng)歷病魔,算得上體面。
七、圓墳
安葬后的第一天,全家人都要去圓墳。所謂圓墳,指的是傷者家屬到墳前行圓墳禮,同時(shí)要紙錢錢、上香、上貢品。
喪禮這天男方只能把棺木送到山下,家里的男人們才有資格把棺木放置地里。所以,這也是我第一次去到父親的墳頭。
那天一早我和爸爸便在父親家打算圓墳要用的貢品:五樣獼猴桃、五樣茶點(diǎn),仍然是雙數(shù)。三姑買來了父親愛吃的西瓜,你們因要不要帶刀去墳上爭(zhēng)吵了一番,最后聽陰陽(yáng)講不要帶兇器掃墓,這才罷了。
我和弟弟、媽媽、伯母?jìng)円黄鹱咧鴴吣梗瑥哪赣H家出發(fā)大約要二十分鐘。媽媽家旁邊以前是一片甘蔗地,三年前政府要求退耕還林,小麥地弄成了一片還未長(zhǎng)得很高的小樹林。雖然農(nóng)田弄成了樹,樹的那一頭,兒時(shí)就在的高鐵一直通大火車。我還讀高中時(shí)每年回村都吵著要弟弟帶我去看火車,男寶寶氣爆棚的她說自己閉著眼都可以走到高鐵這邊,可我們倆的看列車計(jì)劃總因各類事情沒能完成,如今我倆都已成年,不免有些遺憾。
(退耕還林后的樹林岸邊是高鐵)
剛到地方,聽聞人的步伐,墳前一堆覓食的鳥兒一齊飛起,倉(cāng)皇而去。母親的墳旁東倒西歪地插著兩個(gè)花圈,應(yīng)當(dāng)是出殯當(dāng)天放的。這時(shí)我們?cè)侔研∧咀涝趬炃埃瑪[好貢品,點(diǎn)燒香,家里人半圍著墳下跪,同樣是由爺爺和二伯父起先點(diǎn)紙,其他人接著便一齊把香燭推入火盆。
火愈燒愈旺,熱氣上升導(dǎo)致香燭上方的空氣有些扭曲。從我的視角看,父親母親的墳雖然也在搖動(dòng)。與此同時(shí),“娘啊,娘啊”的叫喊聲再度響起,妹妹們和弟媳們哭到站不上去,我們后輩便躺下扶起你們,哭聲也急遽而止。
直至所有香燭燒完,火完全吞并,家里的女性再用鏟子把泥土翻新,蓋在灰燼上以防風(fēng)吹失火。父親和叔叔們也把埋著父親母親的那篇墳地又加固來一遍。這時(shí)天上下起了陣雨,四伯說:“這下死灰不會(huì)復(fù)燃了。”于是,我們回程。
回去的路上,按規(guī)矩我們要把系在胸前的線繩解開。我和弟弟并排走著,她經(jīng)常在路上摘些能吃的葉子和果子給我,有的很嫩,有的很麻。沒怎樣見過世面的我很是新鮮,一路上和她一邊咬樹根一邊聊起舊事。
路過村里的中學(xué),哥哥說她當(dāng)時(shí)在這兒讀書,一至四年級(jí)全在一個(gè)班,一個(gè)班三四十個(gè)人。后來村里人都去外邊打工,兒子跟隨進(jìn)城讀書三鞠躬是給死人祭拜嗎,沒了中學(xué)生,沒了老師,中學(xué)也便關(guān)了門。
進(jìn)家門前按規(guī)矩,每位人要把置于院旁邊木盆里的刀翻個(gè)面,聽說這意味著與傷者今后一刀兩斷,讓活著的人不再受傷者困惑。我不懂為何要一刀兩斷,大人們說:對(duì)您好就是了。
圓墳完畢,我進(jìn)屋脫下孝衣,又走出院門望向這片樹林的另一端。看著一列列車經(jīng)過,耳畔又想起哥哥的話:我小時(shí)候沖起火車招手,總以為它會(huì)在家旁邊停,長(zhǎng)大才發(fā)覺去西站的路就要好遠(yuǎn)。
八、過七
所謂過七,指在人逝世以后每?jī)商炫e辦一次吊祭典禮,通常在第五次或第七次斷七。
按規(guī)矩,你們每周都要紙錢錢。但你們?yōu)榱松疃既ネ饪h工作,妹妹們也搬去他處。在現(xiàn)代社會(huì),已然很難湊到人來完整貫徹這一典禮。爺爺說,不管你們身處那個(gè)城市,在過七的時(shí)侯要記得往家的方向紙錢。
(母親下葬時(shí)忙家人放了二踢腳,讓死亡覺得也沒這么可怕。本人夾帶私貨,送你們這首歌。)
筆者雜記:
喪事,于死人而言是一種體面離開的典禮;于活人而言不僅寄寓追憶故人的心緒,其實(shí)也是家庭關(guān)系的紐帶、回歸故里后對(duì)過往歲月的回憶……
在這場(chǎng)新世代與舊風(fēng)俗的碰撞中,我并沒有摸透何為死亡,也不懂該怎么面對(duì)它。不過,死既然是人生大事,那我也毋須著急,就用一生去漸漸探求這個(gè)課題吧。
這篇雖寫母親的喪禮,腦海中也涌現(xiàn)出與父親、爺爺在村莊里的舊事。她們離開時(shí)我正值小學(xué),很遺憾沒有完整出席過她們的喪禮,明明我與她們的關(guān)系更為緊密。兒時(shí)返鄉(xiāng),幾乎都是她們帶我在村里轉(zhuǎn)悠,看乳牛擠奶、去派出所院里看影片、跟著父親走到農(nóng)田里摘水果、爺爺騎二八單車帶我去對(duì)門村買醬汁肉、過年陪父親站在大貨車上指揮村里扭秧歌……
典禮雖沒有我們所想像的這么重要,但卻能讓我們沉下心追憶過去。其實(shí),喪事,也是一場(chǎng)與過去和解的典禮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