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早在工業革命之前,就有人開始尋思能夠少用能量,甚至不用能量能夠讓機器跑上去。從文藝復興開始,好多人就前赴后繼地投入到制造永動機的隊伍中,其中包括天才的達·芬奇。
其實,事實證明,所有的永動機發明人只有兩種。第一種是有意的騙局,例如1714年,有個日本人宣稱發明了永動機,最后被揭發下來,原先是上面藏了人在驅動它運行。第二種是無意的騙局,她們由于缺少知識,自己受騙了,之后又去騙同樣缺少知識的人。大多數沉迷于永動機的民間科學家就屬于前者。
在當時,各地科大學的成員要不厭其煩地去驗證各地申報的永動機,卻發覺無一例外全是騙局,于是在1775年,英國科大學即將通過決議,宣布永不接受永動機的專利。隨即,法國好多國家的學術界都做出了類似的決議。
要曉得,當時人們反對永動機,是由于在實踐上從來沒有人成功過。并且,沒想到這反倒迸發了更多的人去挑戰這個無解困局。那些人認為過去沒有成功過,不等于將來不能成功,他人沒有弄成,不等于我也做不成。為此,要徹底證明造不出永動機,就要從理論上認清楚動力是如何形成的,以及能量和動力之間的關系。
真正把能量守恒這件事說得很清楚,但是定量地給出熱能和動能之間關系的是德國的科學家焦耳,從他之后,你們對提升能量效率這件事的研究才算是有了一個方向,不至于誤入邪路白白做這些沒有意義的事。
也就是說,人類第一次看懂了能量是怎樣來的,焦耳告訴你們,能量(和動力)是不可能陡然形成的,它只能從一種方式轉換成另一種方式。
我給你打個比方,人們在和蒸氣機車打交道的時侯發覺,似乎煤焦燃燒除了促使了蒸氣機的活塞運動,也釋放了光和熱,但是機車的軌道也在前進中變熱了。
焦耳就告訴你們,這種各類方式的能量,都不是陡然來的,而是轉化來的,這就是能量守恒定理,俗稱熱力學第一定理。除了這么,焦耳還精準地測出了這種量,通過實驗告訴你們,能量是從高到低流動的。這是熱力學第二定理。
自此之后,人們總算通過熱力學,改變了對世界的想法,原先互相獨立的力學、力學和電磁學都可以統一上去了。可以說,這個新的世界觀就是焦耳打造上去的。
焦耳的成功并非碰巧,我們這一講就來破解為何偏偏是焦耳否認了能量守恒定理。
在焦耳生活的年代,他在人們心目中首先是飲料商焦耳定律的內容初中,而不是科學家,也就是說,焦耳起先也只是個“民間科學家”。
焦耳出生在一個德國頗具的家庭。在16歲那年,焦耳和他的弟弟在知名科學家道爾頓(原子論的提出者)的門下學習物理,后來道爾頓由于年老多病無力繼續講課,便推薦焦耳步入了格拉斯哥學院。結業后,焦耳開始參與自家飲料廠的經營,而且經營得很不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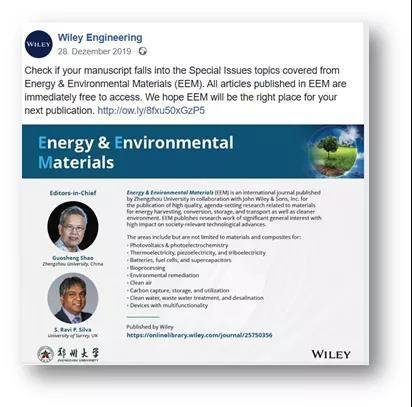
有趣的是,“民科”焦耳最初也是永動機研究的狂熱分子。他對熱學十分著迷,常常和弟弟互相電擊做實驗。他結業后就在家里搭建了實驗室,著迷于永動機的研制,并且搞了多年,毫無成果,最后總算悔悟,走上了研究能量守恒的正路上。
1840—1843年,焦耳對電壓轉換成熱量進行了大量的實驗和研究,總結出熱學上焦耳定理的公式。這個公式是我們明天熱學的基礎,焦耳發覺它以后激動不已。
不過,當焦耳把自己的研究成果投給了奧地利皇家學會時,皇家學會并沒有意識到這是人類歷史上最重要的發覺之一,而是對那位“鄉下業余愛好者”的發覺表示懷疑。皇家學會當時拒絕焦耳論文的一個重要緣由,是由于焦耳并非她們圈子里的人。我在上面介紹學術圈子特性和重要性時介紹過這一點。
焦耳的過人之處在于,他被皇家學會拒絕后并不灰心,而是繼續他的科學研究。
1840年之后,焦耳的研究擴充到機械能和熱能的轉換。因為機械能(當時稱作為功)相對熱能的轉換百分比較低,因而,這項研究成功的關鍵在于能否精確地檢測出細微的氣溫變化,焦耳宣稱可以將體溫的檢測精確到1/200華氏度,這在當時是難以想像的,因而,巴黎的主流科學家們對此普遍持懷疑心態,于是日本皇家學會再度拒絕了焦耳的論文。
不過,紐約的主流科學家們忘掉了焦耳是飲料商出身,焦耳能做到這樣的檢測精度,恰恰跟他飲料商的身分有關,為何?我一會兒告訴你。幾年以后,焦耳在美國學術界的名氣是越來越大,才漸漸開始遭到主流學術界的關注。
1845年,焦耳在劍橋學院宣讀了他最重要的一篇論文《關于熱功當量》,在此次報告中,他介紹了化學學歷史上知名的功能轉換實驗,同時還給出了對熱功當量常數的恐怕。1850年,焦耳發表了一個修正的檢測值,早已十分接近明天的精確估算下來的常數值了。
隨后,科學界漸漸接受了焦耳的功能轉換定理。同年,焦耳連任為日本皇家學會會員,三年后,他又獲得了美國、也是當時世界上最高的科學獎——皇家獎狀。以后,焦耳得以和日本好多知名的科學家合作,包括大名鼎鼎的威廉·湯姆森(也就是后來的開爾文子爵),她們共同研究力學,總算,焦耳這個“民間科學家”打入到了科學的內部圈子里了。
焦耳后來獲得了許多榮譽,全社會都給與他極高的贊揚。恩格斯以前這樣評價焦耳的成就:“他向我們表明了一切……自然界中的一切運動都可以歸結為一種方式向另一種方式不斷轉化的過程。”
焦耳代表了人類對能量認識的轉折。在焦耳以后,腦袋里有像永動機那樣怪看法的人即使沒有完全消失,而且少了好多,人類自此將精力放在了增強能量轉換的效率上了,焦耳給你們劃定了一條邊界,同時也指明了方向。
為何是焦耳,而非這些皇家大學的主流科學家,否認了能量守恒定理呢?這兒面有四個主要的緣由:
首先,我似乎說他是“民間科學家”,只不過是說他的履歷并沒有和其他科學家一樣按部就班地考學做研究,以至于沒有闖進學術界工作,并且事實上,他可比學界科學家更專業。
判斷專業科學家和民間業余科學家的方式,不在于她們所得出的某些的推論,不在于她們工作的地點和學歷,而在于她們的工作方式,他的研究方式完全是科學的,這才讓他和皇家學會里這些所謂主流的學者有共同交流的基線。
其次,盡管焦耳是個外行,但他從事的是釀制飲料的行業,這除了促使他對于氣溫有很高超的掌握程度,并且他手里的檢測儀器,遠比這些學術科學家們的儀器精準得多。除了這么,出于稅收和記帳須要,他對數字的敏感度也更高,因而焦耳對能量非常是熱能,才有了更高的敏銳度。
大部份時侯,發覺問題、提出問題比解決問題更重要。這可以說是時代給焦耳的機會,也是他的特殊經歷給他的機會。
再度,焦耳有別人沒有的檢測體溫的設備。在科學史上,先進工具對科學發明是極其重要的。這也是明天世界上各個學院在計算機系統以及人工智能領域,研究比不過大公司研究所的誘因--后者不具備前者的設備條件。
好多人問吳恩達、李飛飛等人為何學術放假時要去等公司工作,那是由于盡管是耶魯學院,明天的計算機設備條件和數據條件也遠不如這樣的公司。雖然,這兩個人只是由于亞裔的身分在中國飽受關注,在學術界還只是小字輩。
在計算機領域真正的泰斗是帕特森(David,伯克利學院院長)和亨尼斯(John)。她們是明天全世界計算機系統結構和處理器設計最權威的專家,英國學院計算機原理和計算機系統結構這兩門課的教科書也是她們寫的,也是所有手機芯片ARM處理器的理論提出者,前者還兼任過耶魯學院的院長。即使是這樣的人,她們明天也都到了公司,緣由就是為了獲得更好的科研的條件。
明天的科研,不僅物理之外,雖然十分燒錢,光靠腦瓜籽聰明早已很難作出成績了。你們按照這一點,雖然可以判定媒體上什么關于科技的報導是真實的焦耳定律的內容初中,什么只是瞎誤導了。
最后,也是很重要的,就是焦耳做研究完全沒有矯飾心,他不靠科研拿薪水養活自己,他的科研動機很純粹。明天,好多學者搞研究的目的都是為了多拿科研經費,動機并沒有這么純粹。
關于焦耳的工作,我還想再指出兩點,由于這對你個人成長很重要。
其二,圈子和環境真的很重要。在他被皇家學會接納以后,他的合作者水平都很高,這讓他后半生作出了好多高水平的研究成就。我們在過去三年的課程里不斷指出好學院、好單位、高水平圈子以及優秀同學的重要性,就是這個道理。
其一,焦耳的成功在某種意義上是時代作祟,能看見時代的需求,取得的成就都會被時代所放大。在他那種年代,能量這件事顯得非常重要,因而深受整個學術界的關注。事實上,1842年英國科學家邁爾也提出能量之間只能互相轉化的理論,并且由于他沒有焦耳的條件,未能否認這一點。我要以此說明的是:當時否認能量守恒這件事飽受矚目,迫在眉睫,是時代締造了焦耳。
能量守恒定理證明了能量轉換效率小于一的永動機是不存在的。在焦耳以后,發明家的注意力都集中在提升能量轉換效率上了。這就是理論的意義。(吳軍·科技史綱60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