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Peter,歷任日本帝國理工大學化學系中級研究員,美國國家量子技術計劃戰略顧問委員會主席,美國國家數學實驗室量子計量研究所主席。曾任日本帝國理工大學副主任,美國化學學會(IOP)主席(2011-2013),帝國理工大學管理委員會和理事會成員,他也是英國光學學會()的前任主席,基金會的監事。因為在光化學方面的出眾工作,2005年他在法國女王生日封爵名單上被封為爵士。
導讀日前,爵士接受了特邀編輯北京學院馬小松院士的專訪。在專訪中,爵士回顧了量子光學的誕生與發展,介紹了自己歷時60年在量子光學領域的研究經歷。他介紹了自己與中學生在該領域的重要成果,以及發覺這種成果的軼事。他還列出了全球最新的量子科技進展,描畫了可能會對人類社會形成的改革性影響。爵士是美國國家量子技術項目的領導者之一。在采訪中,他追憶了該項目從無到有,從學院延展到工業界、政府部門并共同發展的歷程。現今量子光學領域的許多頂級化學學家都是爵士的中學生。他分享了自己在培養中學生方面的理念和觀點:尊重和欣賞年青人的能力十分重要。在采訪最后,他追憶了20世紀70年代,當他還在康涅狄格學院做博士后期間,與多位量子光學奠基人共進晚餐,討論學術的歲月。時隔近50年,他償還晰記得:當看到(量子光學奠基人之一)介紹雙光子干涉(亦稱Hong–Ou–干涉)的奇特量子現象時,心里的那份激動之情。正是這份對科學的激情與熱愛伴隨著他半世紀的量子光學旅程!
撰稿|馬小松(北京學院)
編輯|丁潔呂璇
馬小松:您為何選擇量子光學作為專業,能分享一下您在量子光學領域的研究經歷嗎?
Peter:20世紀60年代中期,當我還是個中學生,早已開始思索現今稱之為量子光學的東西。量子光學在那時處于發展早期,當量子性質在光學實驗中凸顯下來時,才開始呈現迅速發展的征兆。這一領域最初被稱為“量子電子學”,而“量子光學”則是被極少數關心光量子性質的化學學家所使用的術語。
大專時,我就從事這方面的工作。像許多中學生一樣,為了證明可以做一些原創性的工作,我選擇參與項目——研究光學泵浦。我對制做一個銫原子氣室,并檢測光泵浦過程中的所形成的相干瞬態這一過程很感興趣,但當時我的工作是在射頻范圍內,用極其簡單的實驗和儀器完成的。這種實驗都是用熱光源做的,而不是現今采用的可調諧激光器。
我發覺量子光學十分誘人,也由于我當時做這個實驗的儀器極其簡單,所以讓我有些飄飄然,自覺得可以成為一個實驗化學學家。當我開始攻讀博士學位,做的項目須要理論與實驗相結合時,我很快發覺自己完全不能勝任實驗工作,實驗化學學家于我而言并不合適。當我說“我最好還是轉做理論”時,實驗室的其他人可能都很高興。這段旅程是一個意外,雖然它很誘人。
于是,我的博士階段轉做理論,但在后來的工作中,我仍然與身邊的實驗化學學家保持著極其密切的聯系,與杰出的實驗化學學家交流討論,同做實驗的朋友一起工作。我想這在當時的美國是不尋常的,由于一般理論學家和實驗學家在不同的院系。
取得博士學位后,我去了英國考文垂學院做博士后,與(前日本光學學會主席,國際知名量子光學專家)一起工作。我須要再指出一次,一個真正強悍的理論學家,總是和實驗學家一起工作。我在的團隊中渡過了美好的兩年歲月,與十分偉大的人一起工作,但是第一次真正理解了怎樣成立團隊,怎么規劃常年的職業生涯。
我于1974年回到奧地利。當時整個德國,對量子光學理論感興趣并舉辦相應學術工作的人大約只有四五個。這是極少數人的興趣,但這確實令人激動,由于步入一個新領域的體驗很美妙。當時德國量子光學的領導者之一是謝菲爾德學院的(日本知名化學學家,《光量子理論》作者),同樣地,也與實驗學家密切合作量子物理學家的訪談,他對我的職業生涯有深刻影響。
期間我獲得了多種基金捐助,讓我第一次擁有了研究生。我與法國導師一起共同指導研究生。這段經歷給了我與真正有才氣的人一起解決棘手問題的經驗。只身工作,你可以做一些事情;并且和一群志同道合的人一起工作,你可以做得更多、更好。
1979年,我加入帝國理工大學。我的研究小組擴大了,幾乎成了系里的一個子系,有好多做實驗的同學參與進來。在新加坡工作回到日本的經歷讓我明白,科研活動是國際性的。在與世界各地研究者的合作中,我獲益頗豐,我的團隊在最高產時顯得特別國際化。我相信這對每個人來說都是挺好的借鑒:和世界上最好的人一起工作,你可以做好多事情。
馬小松:您提及在上世紀70年代,在量子光學這一學科萌芽時介入并開始研究是美妙的。現今,量子信息是新興技術,您對量子信息有哪些想法?您覺得我們如今處于這個領域的那個階段?
Peter:這真是個好問題。量子信息科學誕生于量子光學,科研工作者在量子光學領域進行了常年的、大量的基礎研究,量子估算、量子密碼等都是從基礎研究中形成的。實現這種東西須要耗費相當長的時間。在個別領域,我們取得了巨大的進步,但仍有一些困局須要解決。我覺得我們早已對很多化學現象十分接近并具有一定理解。即使推廣這項技術才是真正的挑戰,但我們確實了解了許多事情。
全世界對量子估算有著極大的興趣。人們正在研發出眾的靶機,我們看見中國潘建偉教授團隊近來成功實現了壓縮態玻骰子取樣與超導芯片隨機線路取樣,取得了巨大的進步,證明了量子優越性。
如今,其實只有我一個人在害怕吧,我不覺得我們真的理解量子優越性的起源。為何我們能獲得量子效應帶來的加速?量子優越性的本源是哪些?我們曉得有量子糾纏、相干性、量子非局域性。并且,人們對量子估算的引擎知之很少。是哪些給了我們優勢?我們有一種未知的力量,將為我們在信息技術方面帶來巨大的優勢,但這些優勢的起源仍有待探求。
所以,假定“我如今還是個中學生,會怎么選擇未來的研究方向”,我會回答:假如我重新開始,這是一個真正須要解決的大問題——我們曉得它開始運轉了,而且為何它會運轉呢?順便說一下,我甚少對捐助我們的商界說這句話。
在成熟的領域里,年青的中學生常常有一種覺得,在這個已確立的學科中,年青科學家想取得成就相當困難,由于好多工作早已做了,她們只能做一點點增量或優化的工作。但在一門新學科中,你可以成為游戲規則的擬定者,你可以提供革命性的觀點與方法。
新步入一個領域的研究者可以改變研究主題。我曾經最知名的中學生之一是ArturEkert(牛津學院院長,入選2018/2019年度墨子量子獎)。在他博士生涯的最后幾個月,他提出了基于糾纏態的量子密碼學。事實上,我們關注量子關聯早已有很長時間了。他在貝爾不方程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所以他在博士學位正式結束時進行量子關聯的應用研究是很自然的事情。
在一個新興領域,年青人可以帶來多大的改革。例如牛津學院的,他雖然不是我的中學生,但我很了解他。在他初期的研究生涯中,他與他人共同發明了量子糾錯碼,這對目前大規模的量子估算十分重要。這就是為何在量子信息科學領域,世界上最聰明的一些年青人想要從事這方面的工作。這很吸引人,也有巨大的挑戰,但她們曉得自己可以作出改變。
馬小松:您剛剛提及ArturEkert,他對貝爾不方程、糾纏等的研究主要是基于量子化學學的基礎研究。當時,您和您的中學生是否構想將這些基礎研究轉化為應用?
Peter:現階段的一些數學進展一直須要大量的工程研究。我們可以構建基于糾纏的量子通訊,甚至可以像墨子號一樣,通過衛星在光纖和自由空間中進局長距離量子通訊。量子通訊有巨大的潛力,信息安全的傳輸只是問題的一部份,我們必須才能處理系統的整體安全性。我們須要通過真實儀器的安全性來證明,而不是理想化的儀器。這項工作一直正在進行中,我們不想見到量子通訊系統只在理論層面上是安全的,但在實際工程應用中有缺陷。
我覺得量子通訊的實現和安全性方面還有好多工作須要進一步研究。并且聽到像量子糾纏這樣獨特現象正在蘊育一個新的行業,這是很奇妙的。我見過貝爾本人幾次,我想他會對這一切發展倍感欣慰。貝爾實際上是一個偏實驗的化學學家。他的本員工作旨在于加速器的設計,在職業生涯的大部分時間里是一名加速器科學家,基礎量子化學的理論研究工作是他的業余愛好。我猜他并沒有想到自己的工作會成為一個全新產業的基礎。
量子可以帶來改革,不僅僅是糾纏,還有相干性。雖然,原子相干性是現代技術主要驅動力之一,是全球定位系統、星載原子鐘等的化學基礎。人們沒有意識到,在世界各地的導航和計時系統完全依賴于保持原子載流子相干性。當人們說量子技術是一個仍未證明自己的新事物時,我總是提醒她們,我們早已走了很長的路并取得了成功:全球定位系統依賴于量子相干性,對世界經濟作出了巨大貢獻。
馬小松:我們討論了疊加、相干以及糾纏,這種是量子系統的主要特點,被應用于這場新的量子革命。您覺得還有未被發覺的量子特點可能是有用的嗎?
Peter:就有用性而言,我們開始理解局限在那里、優勢在那里。我們早已在電磁場偵測、引力的量子傳感領域見到了這一點。而且,這種技術發展迅速。我1967年開始從事光學泵浦相關研究,現今我們可以建造十分小的光泵浦系統并用于測量腦部中的電磁訊號,一個真正緊湊的傳感,如同一個單車頭盔,用于檢測腦部活動。這一領域的發展之一是在伯明翰從事量子技術的研究者們,她們建造了一種腦部傳感,早已被診所的內科大夫用于治療肝病。這是一個監視腦部活動的量子傳感,被拿來指導內科大夫的放療刀。真的太神奇了。
有了電磁傳感,可以偵測到其他東西。諸如:在建設新建筑之前須要了解地基情況,那里有隧洞,那里有縫隙等,卻很難弄清楚地下是哪些,因此,在土木工程上早已浪費了大量的資金。但運用量子技術,一個可以檢測重力差的量子干涉儀早已可以告訴你地下是哪些了。世界上有好多人正在建造檢測地面基礎設施的冷原子干涉儀。這很有趣,我們可以勾畫地下世界的地圖,并且毋須耗費數十億去挖掘公路,找出管線在那兒。單粒子干涉儀是量子化學最基礎的實驗之一,而我們正在用它來找出排水管在那里——真是實用和未知的完美結合!
如今我們一直在思索一些更基礎的事情,我們并沒搞懂楚量子估算的力量來自于哪些。在這個領域中所做的大部份工作都是構建在假定之上,即當前對量子熱學的認識是正確的,也就是疊加和線性。真的是這樣嗎?或則從極其靈敏的實驗中獲得證據,證明存在比已知線性量子熱學疊加更多的東西嗎?人們開始思索這個問題,在世界各地,科研工作者開始研究怎樣利藥量子技術的超高靈敏度,測量我們是否真的了解所有的基本自然法則。并且我們向大眾承諾這會奏效。同樣,實驗的敏感性可以幫助探求基礎科學中的新事物。
馬小松:藥量子力學來探求引力效應,對于基礎研究來說是十分有趣的。您的意思是,對于使用高靈敏量子傳感探求引力效應的研究人員來說,這也可能是一個潛在的新領域?
Peter:偵測暗物質是現代數學學的一大困局。人們開始關注量子技術是否能成為偵測暗物質的有用工具。宇宙的大部份是由我們不曉得的東西組成的:暗物質、暗能量。關于宇宙中占主導組成部份的情況量子物理學家的訪談,我們怎么做能夠讓人類知曉呢?量子技術早已開始為怎樣做到這一點提供線索。干涉儀可以偵測到建筑環境中的重力變化,倘若能大規模工作,或許能夠偵測暗物質了。這是世界上一些十分有看法的人正在做的事情。
馬小松:現今量子光學領域的許多頂級化學學家都來自您的團隊。能和我們分享一下您在指導和促進年青科學家和中學生的絕招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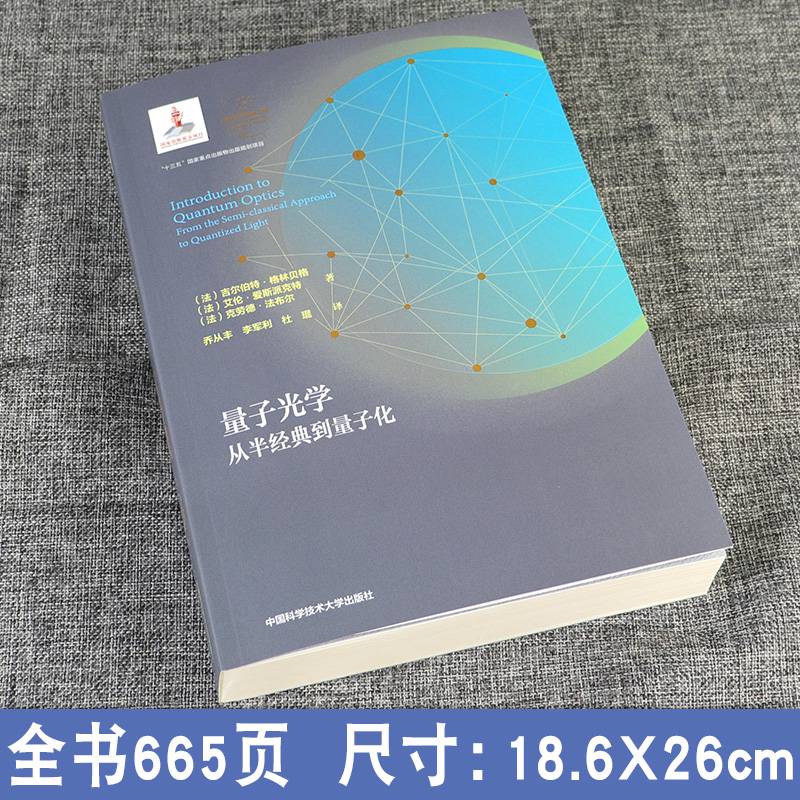
Peter:這沒有哪些秘密,但有些事情很重要。第一,尊重別人。尊重、同情以及欣賞他人的能力十分重要。在個別科學領域,大科學家做了所有偉大的事情,得到了所有的榮譽,其他人兼任著輔助職位,這是個別科學研究的典型工作模式。但在一個新興的領域,這可能不是最好的方式,由于事情在以令人震驚的方法出現。
在我職業生涯的初期階段,在展示獨立性中我確實獲益頗豐。但當我成立自己的團隊時,我早已27歲了,是時侯給年青人獨立成長的機會,畢竟她們能否改變這個領域。我一生中大部分時間是作為一名學院院長渡過,老師的全部意義在于培養,鼓勵下一代學者,這是我們的工作。所以,讓最優秀的人進來,給她們良好的機會,同時找到讓她們盡早獨立的機制。這就是訣竅。尊重她們所能作出的貢獻,整個領域就會獲益。除了這么,就會有優秀的人想和你一起工作。
我將隆重介紹我的一些中學生,雖然她們可能會倍感難堪。我里面提及了ArturEkert,Artur博士結業后立刻獲得了基金捐助,開始獨立承當工作。是我另一位極其聰明的中學生,他也很快獲得了基金捐助,如今是愛爾蘭皇家學會的研究院長。Barry是我的另一位中學生,他在卡爾加里任教。
給年青人一個展示個人學識與潛質的機會真的很重要,她們蓬勃發展,這個領域蓬勃發展,二者相互推動。我覺得指導也很重要,我希望更多的人能更多地關注并指導中學生,由于這才是這個領域真正有效發展的方法。我的中學生,例如,如今是牛津學院的院長;Kim,是我在帝國理工大學的繼任者之一。她們中的許多人都做了特別杰出的工作。
馬小松:據我所知,您是日本構建量子技術項目的領導者之一。您能簡單地給我們講講該項目的歷史嗎?立項之初是否碰到困難?您覺得這個項目在未來5年的發展方向是哪些?
Peter:我們在量子光學和原子化學等領域有良好的科研背景,并得到了外界的認可。2010年前后,操縱和控制單個量子系統,并逐漸應用到具有工程重要性的事務上,是我們項目的重點。
那是一段令人激動的時期,我們開始思索怎么將量子科學轉變為量子技術。在美國,我們在該領域有真正的優勢。但我們意識到,假如能把例如工業、政府部門、大學等合作伙伴團結上去,可以做得更多。國家計劃可以讓每位人都參與其中。我們開始討論這個看法,設法從外界得到一些支持,使得這個項目成功。我們討論了很長時間,忽然間這個項目被推進了。
我記得在2012-2013年,我們為商界寫了關于量子化學學能做哪些的報告,報告篇幅很簡略,然后財政廳長想要一份4頁的總結;之后總統說,能給我一份1頁的總結嗎?后續的進度十分迅速。2013年末,我們就獲得了2.7億美元的資金用于建設這個國家級項目,這在當時是一大筆錢。我們又降低了其他內容,第一個時期的投入總資金約5億,建設了與工業界合作的樞紐。我協助寫了一個三年捐助的愿景,如今有大概10億資金支持項目。這意味著我們可能比其他人更早執行交叉合作項目。
其他國家仍然都有特別強悍的量子科學項目,但協調量子科學的看法相對較新。量子科技吸引了不同領域的專家——工程師、計算機科學家、物理學家、政府人員等等。這真的很有趣。日本量子技術國家計劃聚焦量子傳感器、量子通訊、量子成像以及量子估算等領域,這幾大支柱也早已成為世界范圍內其他研究項目的主要發展方向。歐共體量子旗艦項目反映了這一點,日本的國家量子計劃(,NQI)項目也反映了這一點,所以我覺得我們的基本方向是對的。
馬小松:我相信美國的量子研究人員會謝謝您向政府提倡提供常年穩定的資金支持。據悉,這樣一個國家項目也會激勵其他國家投資量子技術。我們你們都應當十分謝謝您的努力。
Peter:感謝你能這樣說。正是整個量子技術領域的活力、熱情和興趣讓它顯得有價值。看見世界各地正在發生的事情十分激動。我記得當我在佐治亞學院做博士后時,我會和辦公室里的人一起吃晚飯。我周圍辦公室的人有EmilWolf(光化學學先驅,《光學原理》作者),,以及(日本化學學家,量子光學領域先驅)。作為一名年青的研究人員,接觸她們這樣的量子光學奠基人對我來說十分重要。這證明了科學知識是多么令人激動,讓你想真正成為其中的一部份,一生都為之著迷。
量子光學中十分重要的實驗現象是Hong–Ou–干涉——雙光子以一種有趣的形式干涉。我第一次看到這個概念是從它的發覺者那兒:假如你把兩個相同的光子裝入分束器,它們會從分束器的一端輸出,而不是一個光子從一端、另一個光子從另外一端輸出。早餐桌上的其他人問這是真的嗎?當看到那些令人驚訝的事情時,那真是太棒了。這就是為何應當做科學,這是每位人文化體驗的一部份,對新的發展倍感驚訝。
讓我用一個門生的事例來結束明天的訪談,我只能部份地宣稱他是我的門生,由于他不是我的中學生,他和我一起做過一段時間的博士后,后來成為了院長。他就是Terry。
Terry是量子估算公司的創始人之一,對基礎科學做了一些極具前瞻性的思索。公司近來進行了一次重大融資,就在兩周前,納斯達克對其市值為31.5億港元。誰會想到他一直在撰寫精彩的基礎科學論文,同時,作為理論家與O'Brien和Pete等人領導著實驗工作,她們早已用這些方法建造了一個量子引擎,如今價值30億歐元。
Terry研究基礎數學,構建了世界上最大的量子估算公司之一,那是一次驚人的旅程,但這構建在世界各地科學家數六年辛勞工作的基礎上。
Terry是美國人,但他是在英國和南非長大的。O'Brien是俄羅斯人。這些集體合作的能力,讓世界上最好的人和我們一起工作的能力,真的很有趣。中國有潘建偉和他的團隊,在實現大規模量子網路和實現量子估算優越性方面取得了世界級的成果。世界各地的科學領導者正在改變人類。
注:中文已全文刊載于2021年,歡迎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