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盤點近些年來的科技熱詞,“量子”肯定能納入其中。但談論的人多,理解的人卻依然寥寥。
量子熱學除了徹底改變了人類對世界的認知,也將使我們的生活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但量子到底是哪些?科技領域有何研究進展?將為我們帶來哪些?在近期第二十三屆中國文聯峰會上,全省政協委員,中國文聯副主席、中國科大學教授潘建偉以“新量子革命”為題,為我們解答了眾多疑惑——
量子熱學塑造信息技術發展
在人類歷史上,產業革命總是和科學革命緊密相連,而以信息技術為代表的產業革命主要是構建在量子熱學和相對論的基礎上。
所謂“量子”不是某種系統或某種物質,而是對我們構成物質最基本單元的總稱,是能量最基本的攜帶者,它的基本特點就是不可分割性。
事實上,量子是我們的老同學。量子熱學為信息革命提供了硬件基礎,激光、半導體晶體管、芯片的原理等都緣于量子熱學。
“正如晶體管是計算機的基礎,激光技術是現代互聯網的重要支撐潘建偉 量子通訊,導航技術的發展離不開原子鐘等精密檢測技術的支撐……量子熱學的構建直接催生了現代信息技術的發展。”潘建偉覺得,“經過百余年的發展歷程,量子熱學早已為解決我們目前遇見的一些問題做好了技術上的儲備。”
為什么提出“新量子革命”?是由于隨著技術的發展,量子科學技術出現了新的方向和新的生命力。學界對量子領域的研究早已從被動觀測轉為對量子狀態進行主動操縱,被稱為“第二次量子革命”。
具體到信息技術發展領域。一方面,信息安全是信息技術進一步發展的重要困局,目前的網路信息安全每天都面臨著嚴重的恐嚇。大約在100多年之前,你們就開始討論,以人類的才智,究竟能夠構造出一種人類自身不可破解的密碼?
另一方面,隨著人工智能和大數據時代的到來,估算能力的需求進一步降低,須要找到一種新的途徑。
在這樣的背景下,借助量子的基本性質,促進信息科技的進一步發展就成為科學家們孜孜不倦的追求。
據潘建偉介紹,目前量子信息科學主要才能提供兩種應用方法:一是無條件安全的信息傳輸方法;二是提供超快的估算能力,闡明復雜系統規律。

具體來說,因為量子不可分割原理,假若信息被他人取走,最后的接收者將收不到秘鑰,也就不能拿秘鑰進行信息傳遞,這樣可以保證加密內容不可破譯;再加上量子熱學覺得,不可能把一個粒子的狀態信息精確“拷貝”一份而不改變它本身,即量子態是不可復制的,保證了量子分發本身的安全性。
在估算方面,量子論和精典數學的最大不同,就是它覺得事物狀態并不是惟一確定的,而可以是各類可能性的“疊加”。如傳統計算機處理信息的最小單位比特,要么是0要么是1;但在量子論看來,一個比特處于0和1的疊加態,被稱為“量子比特”,借助這些性質處理數據時可以并行運算。換句話說,傳統計算機一次只能處理一個信息,而量子計算機一次可以處理N個信息的疊加,估算效率大大增強。為此,量子估算具有強悍潛能,可用于精典的密碼破譯、氣象預報、金融剖析、藥物設計等。
走在前列的量子通訊技術
2016年8月,“墨子號”量子科學實驗衛星在蘭州衛星發射中心發射升空。這是世界上第一顆量子衛星,為我國推動世界量子通訊技術發展奠定了堅實的科學與技術基礎。
“墨子號”是我國在過去20年間大力發展量子信息技術的一個注腳。“量子信息技術早已成為歐美主要發達國家的一個重要戰略布局。但由于我國在這個領域起步較早,也得到國家注重,所以始終保持一定優勢。”
據潘建偉介紹,針對廣域量子通訊的發展路線,國際上有3種發展路線:通過光纖實現城域量子通訊網路;通過中繼器實現城際量子通訊;通過衛星中轉實現遠距離量子通訊。
我國在實用化城域光纖量子通訊網路方面早已取得了較多進展。如2007年,實現了光纖量子通訊的安全距離首次突破100公里;2008年,建成首個全通型城域量子通訊網路;2012年,建成46個節點的規模化量子通訊網路,并將“基于量子通訊的宜春全通訊保障系統”投入永久運行。
在基于可信中繼的城際量子通訊網路方面,我國已完善光纖總長超2000公里的滬寧干線,目前正式轉到商業營運。
而第三種發展路線——在全球范圍內覆蓋各種海島、遠洋船舶、駐外機構等光纖無法或則未能抵達的地方,“墨子號”的發射彌補了這一空白。
潘建偉說,目前“墨子號”已順利完成了三大科學實驗任務。“我們實現了上海和哈爾濱之間遙遠地點的量子分發潘建偉 量子通訊,后又完成了單向量子糾纏分發和遠距離量子隱型傳態實驗。在此基礎上,完成了‘墨子號’和滬寧干線的對接,實現了洲際量子保密通訊;并對量子熱學與引力的融合進行探求。”
實現“量子估算優越性”
在量子估算領域,因為其本身對環境的干擾十分敏感,潘建偉強調,真要造出一臺通用的量子計算機大約還須要20年甚至更長的時間,由于會涉及幾百萬量子比特的相關操縱。為此,學劃分義了3個階段性的目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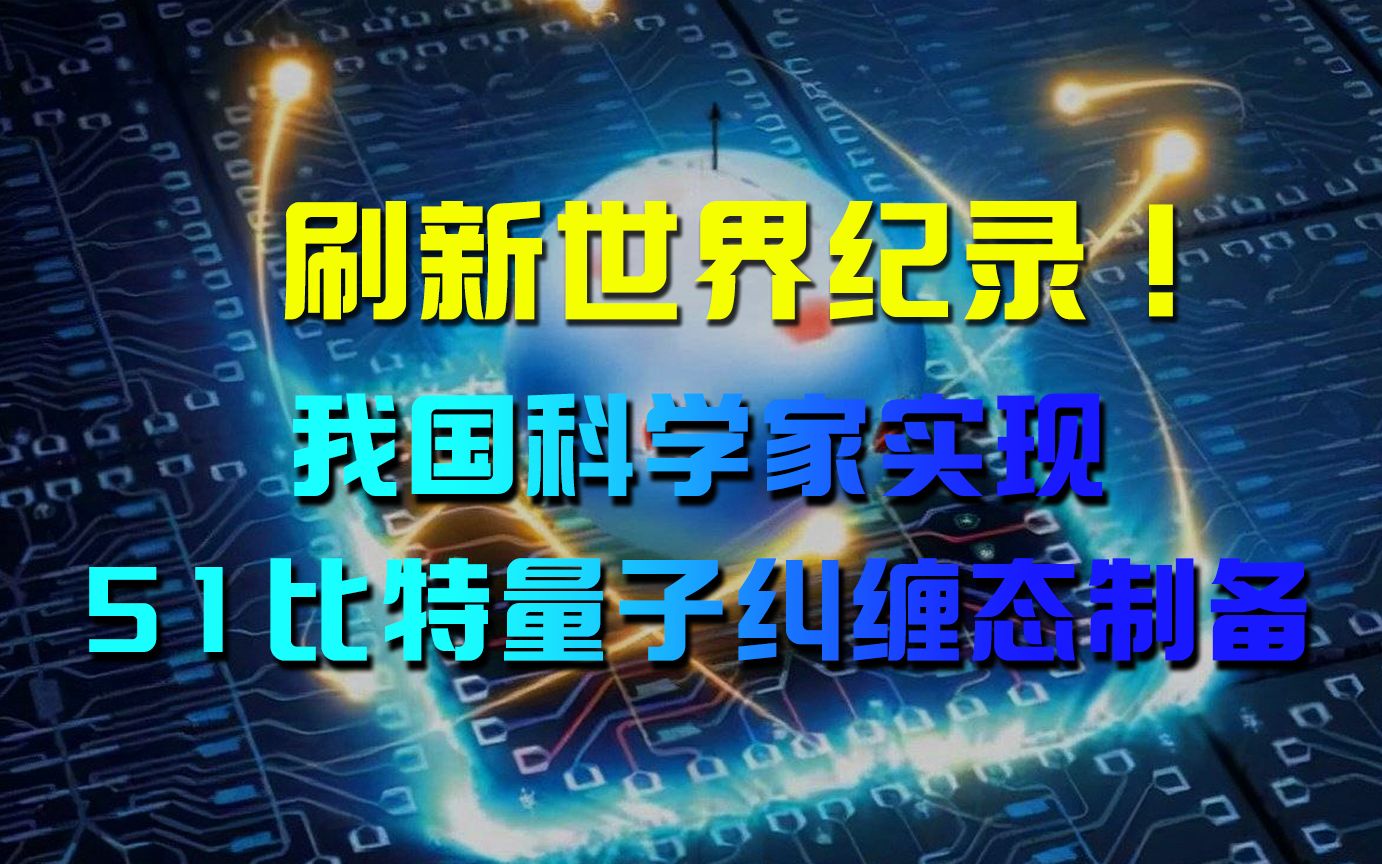
第一階段是才能操縱50到60個量子比特,使處理個別特殊估算問題時趕超傳統計算機;第二階段是還能操縱數百個甚至數千個量子比特,建立某種專用的量子計算機和量子模擬機,闡明個別精典計算機難以解決的復雜化學系統的規律;第三階段是建立可編程的、通用的量子計算機。
我國在這種方面已取得了比較好的進展。
據介紹,潘建偉團隊在2017年便建立了針對多光子“玻色采樣”任務的光量子估算截擊機,這是歷史上第一臺趕超初期精典計算機的基于單光子的量子模擬機。
2020年年末,我國成功建立了76個光子的量子估算靶機“九章”,實現了具有實用前景的“高斯玻色采樣”任務的快速求解,比當時最快的超級計算機快100萬億倍。并且近來又進一步升級,提升到113個光子,比2020年的結果提高了10個數目級。
據悉,我國在超導量子估算方面也取得較好進展。
2019年初,中科院量子信息與量子科技創新研究院實現了12個量子比特糾纏“簇態”的制備,保真度達到70%,打破了往年10個超導量子比特糾纏的紀錄。
2019年末,微軟公司建立了53個比特的超導量子估算系統。
而去年5月,我國已成功研發出62個比特可編程超導量子估算靶機“祖沖之號”,估算能力比微軟的快3個數目級。目前,已進一步提高到66個超導比特,比微軟的快5個數目級。
潘建偉說,我國是德國之外惟一一個在光量子估算及超導量子估算兩個系統都實現“量子估算優越性”的國家。
“目前,我們正在向量子估算的第二個目標努力,即用量子模擬機解決重要的科學問題。如研究低溫超導的相死機制,促使量子材料本身的發展,預計會在3至5年有較好進展。”
同時,潘建偉希望通過10到15年的努力,發展出才能支撐未來天地一體廣域量子通訊的相關應用;借助10年左右的時間,實現操縱數百萬量子比特,為通用量子計算機的研究奠定基礎。
(記者王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