介紹
中俄科技博弈背景下,中國科學(xué)該何去何從? 您如何看待中國科學(xué)自身的發(fā)展階段以及與國際先進水平的差距? 解決卡臂問題的關(guān)鍵是什么? 中國科學(xué)什么時候真正崛起的? 近日,國家自然科學(xué)基金委員會原秘書長、中科院教授楊偉接受了《知識分子》欄目專訪。
楊衛(wèi)表示,中國基礎(chǔ)科學(xué)研究的進步令人矚目。 大多數(shù)學(xué)科發(fā)展迅速,科研論文質(zhì)量逐步提高,青年科學(xué)家快速成長,國際合作不斷加強。 但總的來說,具有高影響力和原創(chuàng)性的作品仍然很少。 中國科學(xué)研究未來的希望在于一批有前途的青年科學(xué)家。 在日本打壓的國際背景下,中國需要進行全方位的戰(zhàn)斗,不僅在基礎(chǔ)研究上,在卡臂技術(shù)上也是如此。 解決問題的關(guān)鍵在于注重以需求為導(dǎo)向的基礎(chǔ)研究和基礎(chǔ)研究的快速轉(zhuǎn)化。
楊偉,固體熱學(xué)家,中國科學(xué)技術(shù)大學(xué)教授。 年輕時是知青,后獲英國布朗工程學(xué)院博士學(xué)位。 在北京大學(xué)學(xué)習(xí)和任教26年,后任國務(wù)院學(xué)位委員會辦公室科長、教育部學(xué)位管理與研究生教育司司長、主任2006年獲福建大學(xué)博士學(xué)位。2013年任國家自然科學(xué)基金委書記。 2018年回到交通大學(xué)擔(dān)任交叉學(xué)科熱力學(xué)研究中心主任,為大學(xué)生講授通識課《通用力學(xué)》。 同時,他還擔(dān)任多項社會職務(wù),包括中國科學(xué)技術(shù)大學(xué)主席團成員、中國科學(xué)技術(shù)大學(xué)科技部主任、中國科學(xué)技術(shù)大學(xué)科學(xué)顧問等。上海市科技創(chuàng)新中心,中國學(xué)位與研究生教育學(xué)會候任會長。
專訪|李曉明
整理 | 夏志堅
●●●
1、中國的基礎(chǔ)科學(xué)研究進展有多快?
《知識分子》:大約三年前,作為國家自然科學(xué)基金委書記,您曾預(yù)測,2020年中國科技論文質(zhì)量和影響力將達到中等水平,科研誠信度將提高。 現(xiàn)在回過頭來看,中國科學(xué)家發(fā)表的高影響力論文的數(shù)量確實像預(yù)測的那樣迅速下降。 僅去年前8個月,中國學(xué)者就在《細胞》、《自然》、《科學(xué)》三大國際頂級期刊發(fā)表論文117篇。 如何評價中國基礎(chǔ)科學(xué)研究的進步? 在國際比較中處于什么水平?
楊偉:過去10到15年,對中國基礎(chǔ)研究的批評很多。 批評是為了更大的進步。 總體而言,發(fā)展較快,主要表現(xiàn)在四個方面。
一是大多數(shù)學(xué)科都處于快速發(fā)展階段。 記得十二五規(guī)劃是2010年制定的,那時候中國的學(xué)術(shù)影響力是世界第十。 中國科學(xué)技術(shù)大學(xué)提出,到十二五末,我國可挺進世界第五。 當(dāng)時很多人認為是草率的,結(jié)果2013年就提前實現(xiàn)了目標(biāo)。2013年,我加入國家自然科學(xué)基金委的時候,正準(zhǔn)備制定“十三五”規(guī)劃。 制定的指標(biāo)之一是到2020年中國學(xué)術(shù)影響力世界第二,實際上在2017年就實現(xiàn)了。所以發(fā)展比我們預(yù)期的要快一點點。
現(xiàn)在ESI一共統(tǒng)計了22個學(xué)科。 如果以近六年累計被引次數(shù)()來衡量學(xué)術(shù)影響力,我國物理、材料、工程三個學(xué)科已經(jīng)位居世界第一,還有八九個學(xué)科位居世界第一。 1 兩個。
二是質(zhì)量逐步提高。 有一個判斷科研文章質(zhì)量的指標(biāo)叫領(lǐng)域加權(quán)引文影響因子(Field),國際上科研文章的平均值為1,中國1999年前后為0.3-0.4,遠低于低于世界平均水平。 到今年,中國基于文獻數(shù)據(jù)庫的FWCI為1.02,而基于Webof數(shù)據(jù)庫,中國已經(jīng)達到1.06。 這表明,在數(shù)量下降的同時,中國科研論文的質(zhì)量也在提高。 因為只有引用率的上升速度超過了學(xué)術(shù)產(chǎn)出的上升速度,平均影響因子才能上升。
從另一個角度來說,產(chǎn)出質(zhì)量可以根據(jù)全球高影響力研究工作(如全球前1%的高影響力論文)占整個學(xué)術(shù)產(chǎn)出的比例來定義,等于1%就是世界平均水平. 從國際大學(xué)群體比較來看,愛爾蘭常春藤大學(xué)的比例約為5%,是世界平均水平的五倍。 第二組是( of ),它有大約70個校區(qū),包括一些日本和德國最好的中學(xué)。 他們的比例約為3%,最近增加到2.7%。 第三組是日本的羅素集團(Group),包括牛津、劍橋等20多所高校,其比例接近3%。 另外臺灣還有一個RU11(英文: ),包括臺灣11所研究型的國立大學(xué)和公立大學(xué),包括東京學(xué)院、京都學(xué)院、慶應(yīng)義塾大學(xué)等,他們的指數(shù)在1.5左右%。 2008年中國C9聯(lián)賽剛成立時,這一比例約為0.7%。 2011年超過了美國的RU11,現(xiàn)在已經(jīng)達到2.5%左右。 因此,我們預(yù)計到2021年達到AAU和Group的水平。
第三個特點是年輕人在成長。 基金會委員會的一般項目對所有年齡段的人開放。 2010年,據(jù)我們統(tǒng)計,這個項目的主持人年齡高峰在46、7歲。 但現(xiàn)在是一個比較寬泛的年齡高峰,高峰在36、7歲,很明顯是年輕人沖上去了。
此外,留學(xué)歸國的年輕人數(shù)量明顯增加。 十多年前,每出國七人,就有一人回國; 現(xiàn)在基本是七人出,六人回去。 我們所有人才計劃的申請都在持續(xù)下降。 過去,大約20%的優(yōu)秀青年被選中,而今年只有6%多一點。 比如年輕人,當(dāng)初基金委評估的時候,基本上選了三分之一的人,現(xiàn)在已經(jīng)接近十分之一了。 慶前選拔了約600人,申請人數(shù)每年都在減少,說明更多的年輕人聽說國外情況好就回去了。
四是國際合作不斷加強。 這個強化是-up(自下而上)強化,不是自上而下(top-down),不是國家間簽訂大合同支持一批合作。
中國目前在國際合作方面世界第二,日本第一,官方合作很少,都是研究人員自發(fā)的。
很難說國際合作是由國家推動的。 比如NSFC跟英國合作,只能在一些領(lǐng)域做,比如傳染病,因為是全球性的挑戰(zhàn)。 而生物物理學(xué)方面的研究,也給開展跨國合作帶來了困難。 研究全球氣候變化、環(huán)境污染、生物多樣性是可以的,但是因為生物多樣性是全球性的研究和合作,具有全球?qū)傩裕x不開你。 和材料科研合作不好,需要初步審查,比如結(jié)構(gòu)材料是不是和民航底盤有關(guān)? 納米材料是否與新一代微電子有關(guān)? 這些領(lǐng)域很難與之合作。
所以全球性的研究或者叫國際大挑戰(zhàn)的研究比較容易和官方合作,其他都是民間合作。 所謂民間項目,不是國家資助的國際合作項目。 可能雙方都有各自政府捐助的資金支持這些交流。 中國對日合作的產(chǎn)出目前約占整個國際合作產(chǎn)出的一半。
2. 高影響力、里程碑式的工作,原創(chuàng)作品較少
《知識分子》:當(dāng)今基礎(chǔ)科學(xué)研究的主要不足是什么?
楊偉:總體來說,高影響力的作品、里程碑式的作品、原創(chuàng)性的作品比較少。 例如,一個子學(xué)科在其發(fā)展過程中有幾個里程碑,很少有以中國人的作品命名的。 學(xué)科門類的開山之作,原創(chuàng)性的作品就更少了。
比如現(xiàn)在人工智能發(fā)展比較快,如果你列出一百來個重要的作品(比如維基百科引用的那些),很難找到來自中國的作品。 再比如基因編輯,在生命科學(xué)領(lǐng)域非常火爆,而最重要的崗位中國人很少。
2018年全球前1%的高影響力論文數(shù)量,中國跟意大利和法國很接近,達到他們的90%左右,而我們的top千分之一,萬分之一的研究還是比較少的.
另外,我國幾個學(xué)科的ESI排名還比較靠后,與世界先進水平還有較大差距。 一是空間科學(xué)。 事實上,中國的航天技術(shù)非常強大。 現(xiàn)在它號稱世界第三,它的空間科學(xué)是第13。 主要是我們的天文隊伍比較小,只有十幾個學(xué)院有天文系。 第二個是心理學(xué),大概排名最低,世界第十五。
《知識分子》:在提高我國基礎(chǔ)科學(xué)研究質(zhì)量方面,未來的工作重點應(yīng)該放在哪些方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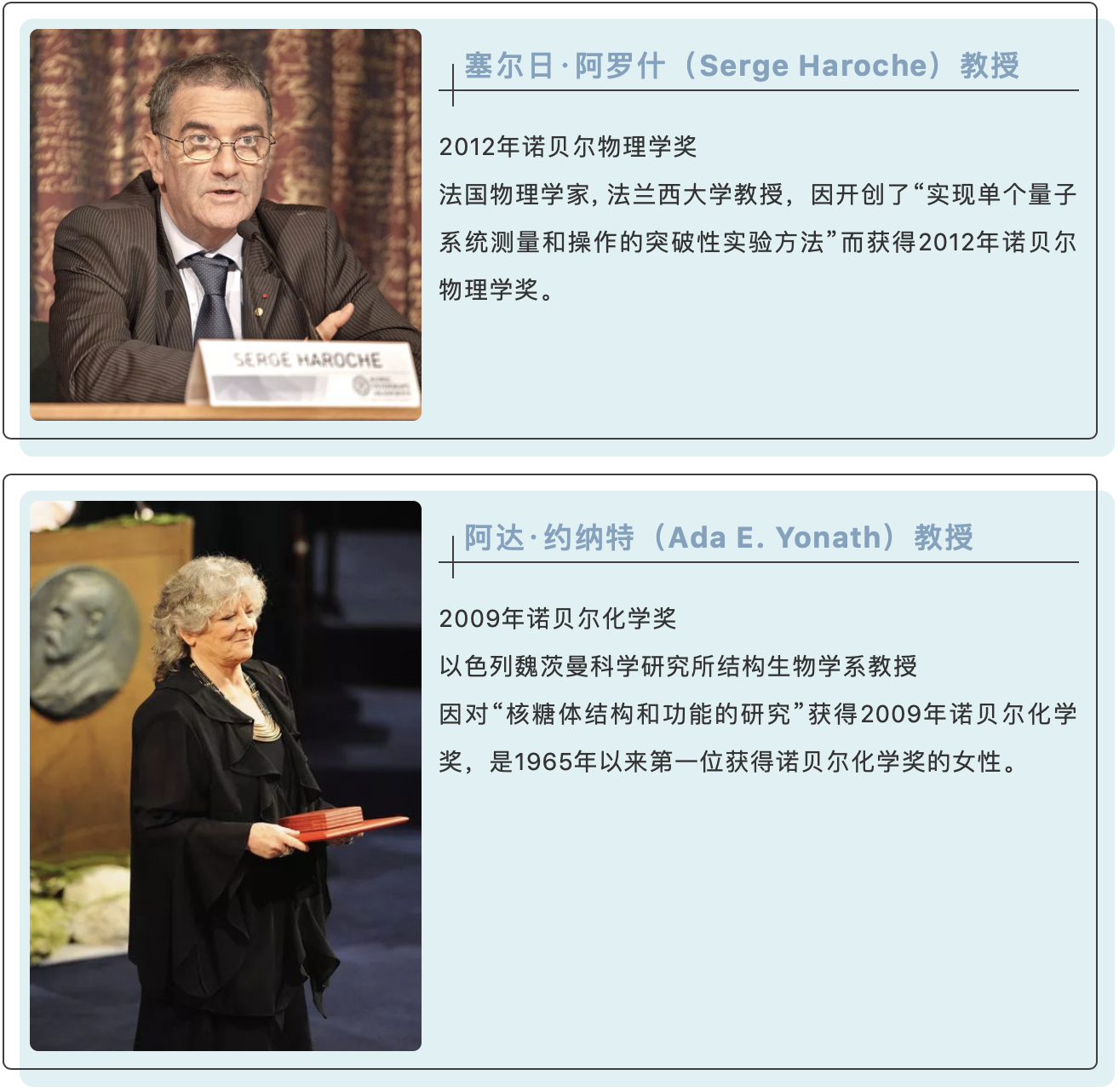
楊威:我覺得我們應(yīng)該支持一些更愿意去自由探索的年輕人。 我們現(xiàn)在的基金項目是分步匹配,類型不一,我個人覺得有個問題,現(xiàn)在申請的人太多了,年輕人拿到捐款的難度比較低。
如今,每年約有 20,000 人申請該基金。 世界上沒有哪個國家有這么多申請者,法國只有6000人。 有的人其實不適合做基礎(chǔ)研究,但是因為單位的一些新政策,如果沒有國家基金項目,不利于個人發(fā)展,所以申請了。
而且我們的選擇率應(yīng)該不會太低。 現(xiàn)在我覺得20%比較合適。 申請的人太多了,所以我們每個項目的捐贈難度都比較低。 特別是我覺得年輕人的捐贈硬度比較低,兩年才20多萬,一年不到10萬。 所以年輕人還是要搞幾個地方項目,幾個垂直項目,你有多少時間去學(xué)習(xí)?
支持現(xiàn)在有能力的年輕人,讓他們安定下來,做自己想做的事。 而且,選擇年輕人的難度更大,比如潔青、有青和青倩。 選好后,變成禮帽,失去了初衷。
《知識分子》:禮帽滿天飛的現(xiàn)象確實嚴(yán)重。 如果年輕人最終爭奪各種禮帽和榮譽,或者貝雷帽背后的某些利益,這可能會干擾他們對科學(xué)研究的專注。
楊偉:我2013年在網(wǎng)上寫過一篇文章(社論),是關(guān)于中國學(xué)術(shù)誠信的。 它提到,如果在各級政府和教學(xué)科研機構(gòu)建立一個人才等級階梯,這實際上會鼓勵你一個一個地去爭奪圍巾,然后把它變成一個(層次),然后逐級上去。部分。 ,這可能會引發(fā)學(xué)術(shù)誠信問題。 爬上去就是千軍萬馬的獨木橋,有的人開始想各種技巧,目標(biāo)就是爬,不是搞好科學(xué)問題。
《知識分子》:人才評價難是個老問題。 2018年7月,中辦、國辦專門發(fā)文指出,要打破四個標(biāo)準(zhǔn),實行代表作評價制度,突出標(biāo)志性成果的質(zhì)量、貢獻和影響。 您認為這些行政措施能否從根本上解決問題?
楊偉:沒有徹底治愈。 破“四只”主要不是破“四”,而是破“只”。 所謂“唯一”,就是將各種指標(biāo)轉(zhuǎn)化為一維排列,然后按照這種排列組合起來,形成一個指標(biāo)。 為什么會產(chǎn)生這些方法呢? 由于需要進行廣泛的非同行評估,包括執(zhí)行評估。 如果有全省的評價,那就確定那個指標(biāo),那個就變成圍巾,就變成“唯一”。 其實評價中的這種指標(biāo)也是屢試不爽,算是比較靠譜的,但問題是過于簡單了,因為個性總是有不同類型的,“只”抹殺了個性。
《知識分子》:因此,一個校園或一個科研機構(gòu)的領(lǐng)導(dǎo),需要客觀地看待各項指標(biāo)和圍巾。 因為科學(xué)研究本身就比較異類,個性比較強,很難有一個統(tǒng)一的標(biāo)準(zhǔn)來判斷。
楊偉:我給大家講講我當(dāng)市長時考院長的過程演變。
院士評價之初,我們是純粹的專家學(xué)術(shù)評價,由專家的主觀判斷來決定。 比如去年中學(xué)有100名院士,所以我們從各學(xué)科招收院士,把100名候選人的材料發(fā)給大家。 每個候選人由一個人介紹。 介紹完了,你投票,一個人,一票。 最后投票的結(jié)果,發(fā)現(xiàn)哪個學(xué)科的專家少,哪個學(xué)科吃虧,就有這樣的問題。
怎么做? 后來改為先查,其實是客觀指標(biāo)。 比如人事部門內(nèi)部掌握的打分??制度,每個候選人做一個績效補充報告。 事后將這一成績與中學(xué)整體成績進行核對,看是否有虛報。 做完之后,根據(jù)你認為的表現(xiàn)的重要程度加上權(quán)重,并據(jù)此算出一個分數(shù),可以作為投票時的參考。 這樣一來,通常分數(shù)高的就是分數(shù)最高的,結(jié)果最后的開發(fā)就變成了只看分數(shù),越來越依賴分數(shù)。 之后,有人開始爭論分數(shù)是否準(zhǔn)確,公式是否準(zhǔn)確。 有人認為公式不夠細化,越細化越“獨特”:比如第一作者算0.5分,通訊作者算分數(shù)分等。 , 而出版物的相對重要性使這些觀點變得更加復(fù)雜。 之后,老師之間的合作出了問題。
比如我們都是第一作者,但是一定要有一個人在前面,另一個人在前面。 雖然貢獻一樣,但是兩個加起來是0.5分,那么第一個還是0.3分,第二個是0.2分。 所以量化越來越細之后,就會出現(xiàn)問題。 參加院長評定的人,都會思考如何短而順利地評出院士。 比如一個人寫一篇文章,發(fā)表在影響因子稍低的期刊上,雖然我不配合,但最后我的分數(shù)還是比較高的。
因此,如果以客觀評價為主,只要不斷放大其指標(biāo)重要性,就會出現(xiàn)問題。 所以現(xiàn)在不干這個了,積分沒了,改成了代工制。 這仍然存在問題。 比如你相信主觀專家的介紹,你介紹的人越好,他的權(quán)重就越大,之后你介紹的人會分為三五九等。
其實,我們總能發(fā)現(xiàn)評價體系的問題,并不斷克服出現(xiàn)的問題,這是一個進步的過程。
3.諾貝爾獎不能計劃
《知識分子》:很多人批評現(xiàn)在的校風(fēng)過于浮躁,流行跟風(fēng)追熱點。 你對這個問題有什么看法?
楊偉:我問過諾貝爾獎評審委員會如何評價諾貝爾獎。 他說我們有兩個標(biāo)準(zhǔn)。 第一個標(biāo)準(zhǔn),如果你是門,沒有人做冰箱,那你就做智能冰箱。 這不; 別人做冰箱,你可以做空調(diào),但你得另辟蹊徑。 第二個你需要的是開門后,不斷有人進來,就是成為一個熱點,不一定特別火爆,不斷有人跟著,從而推動整個學(xué)科向前發(fā)展。
所以如果你只跟熱點,跟跟跟,就會跟到別的地方,到頭來還是不離根。
《知識分子》:如果在某個領(lǐng)域投入更多的資金,吸引更多的優(yōu)秀人才,是不是可以形成更多的門?
楊偉:門真的是資金堆不起來的。 比如給你一大筆錢,你能做到嗎? 給你一個億,你也未必能拿到。 你不知道這扇門是什么。 其實有人能得到,但說不定十個人九個都得不到,所以這是高風(fēng)險高回報。 而且經(jīng)常從審計的角度,一共支持了十個項目,九個失敗了,還有一個不知道行不行。 這個怎么做? 國家的錢就讓你這么花,好像有問題。 因為確實有人誤導(dǎo),有人偏頗,可能還有很多人誤導(dǎo),認為理所當(dāng)然。
我們當(dāng)時跟諾貝爾委員會談過,中國怎么辦? 他說我不知道??你應(yīng)該怎么做,但我可以告訴你什么最好不要做——你不能做任何諾貝爾項目或諾貝爾計劃。
《知識分子》:本世紀(jì)初,我們的鄰國瑞典在“第二次科技基本計劃”中提出,50年內(nèi)要頒發(fā)30個諾貝爾獎。 計劃的時間還沒過去一半,目標(biāo)已經(jīng)完成了一大半。 臺灣諾獎計劃是怎么做到的?
楊偉:法國這樣做的原因比較復(fù)雜。 80年代初期,甚至70年代,臺灣都是有錢的。 想發(fā)展高新技術(shù)企業(yè),日本卡殼不肯松手。 當(dāng)你提到一個目標(biāo)時,找到一群你認為更好的人,然后搜索你想找到的東西。 其實,后來獲獎的就是這批人。
它有幾個條件。 首先是這群人已經(jīng)具備了良好的科學(xué)素養(yǎng)。 與我們改革開放之初不同,大部分研究生沒有讀研。 當(dāng)時美國那些人已經(jīng)有了很好的基礎(chǔ),也有這方面的能力。 二是有相對的修身環(huán)境,可以支持需要比較大經(jīng)費的研究。 而那些科學(xué)家們更是意志堅定、不屈不撓,六年來他們?yōu)樗麨椤?span style="display:none">GBR物理好資源網(wǎng)(原物理ok網(wǎng))
美國之所以在20年前提出這個計劃,是因為經(jīng)過一段時間的考察,發(fā)現(xiàn)有幾個項目還有中標(biāo)的可能,才提出來的。 那時,一些研究工作已經(jīng)基本完成,也就是說門已經(jīng)存在了。 如有必要,更多人可以引用他們的作品或推廣他們的作品。 隨后,美國前往斯德哥爾摩,將這些人介紹給諾貝爾獎評審團。
臺灣的18個諾貝爾獎,從工作到頒獎平均需要28年,相當(dāng)于現(xiàn)在的獎項是在90年代初或更早的時候工作。
1990 年代初我們有什么? 現(xiàn)在想一想你在 90 年代初期做過什么,有可能從事什么工作?
《知識分子》:中國科研的現(xiàn)階段是不是有點像80年代的德國?
楊偉:有點像,但也有一些不同。
首先,由于中國人口眾多,中國的崛起是一次偉大的崛起。 美國已經(jīng)上升到一定規(guī)模,就是每年都有一兩個獎項。 未來中國的科研真的會上升,不是一年一個這樣的量級,大約是一年兩三個這樣的量級。 這是一個不同的地方。
第二,剛才提到美國基礎(chǔ)科學(xué)研究的興起,是在其高科技發(fā)展受到日本阻撓的階段,所以才開始做長遠打算,投入資金進行長期的基礎(chǔ)研究,而且那時候相對來說是錢多了,修養(yǎng)多了。 而中國現(xiàn)在正處于全面戰(zhàn)爭之中。 不僅需要開展基礎(chǔ)研究,還需要開展諸如吐舌頭等技術(shù)。 不能像美國那樣。 如果卡住,您將暫時停止移動。 所以這個是不同的。 中國不可能把所有的資源都局限在一個領(lǐng)域,要協(xié)調(diào)發(fā)展,所以科研的崛起可能需要更長時間。
第三,在科學(xué)傳統(tǒng)和學(xué)術(shù)生態(tài)方面,我們也不甘落后。 我國有一群人是美國留學(xué)歸來的。 他們師從名師,受過良好的訓(xùn)練。 他們知道如何做高水平的工作。 并且有相當(dāng)一部分人不會做高層次的工作。 他們只知道如何跟上高層的工作。
《知識分子》:所以未來基礎(chǔ)科學(xué)的進步取決于今天年輕科學(xué)家的發(fā)展。
楊偉:對。
4、中方如何處理卡舌?
《知識分子》:昨天提到臺灣被德國打壓。 中國也面臨著類似的情況。 很多人認為,如果中俄要在技術(shù)上脫鉤光現(xiàn)象科技小論文初二,可能會在很多領(lǐng)域受到英國的阻撓。 你怎么看待這件事? 在目前的情況下,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
楊偉:脫鉤不一定。 你說中國科學(xué)家和德國科學(xué)家根本沒有交流。 這不太可能,除非兩國聯(lián)手。
當(dāng)卡在手腕上時,有兩個誘因需要考慮。 首先是你有沒有舌頭可以被別人塞住; 第二個是你是否有可能卡在別人的肩膀上。 大國和小國的情況不同。
一個大國想站在小國的肩膀上。 小國的工業(yè)體系和科技體系不完備,大國堵住你的不完備,你就發(fā)展不起來。 大國更難卡在資源上。 如果說我們卡在了日本的稀土礦上,那我們可以做一些事情,但做不了大事。 它所有與稀土相關(guān)的產(chǎn)業(yè)都不會因此而萎縮。 不僅是中國,日本也可以從其他地方買到稀土,但是有的地方是受保護的,所以可以多花點錢開采。 日本也可以封鎖我們的石油,但我們也會找到解決辦法。
但是,技術(shù)可以卡住。 技術(shù)可以分為高端和高端。 高端可以是高端。 因為高端的門檻低,可以自己做。 所以,現(xiàn)在大部分都是高端的,發(fā)展路徑很長,比如微電子,航空底盤。
比如民航底盤的研發(fā),我們要用兩三年六年的時間才能縮小與高端水平的差距,現(xiàn)在一張卡給你卡。 我們在微電子領(lǐng)域落后了 10 到 15 年。 微電子行業(yè)是通吃( takes all),也就是說你的產(chǎn)品稍有劣勢,就沒有國際市場。 中國不可能直接從通吃的目標(biāo)出發(fā)。 我趕不上你最好的,只能慢慢追趕,維持自己的系統(tǒng)。
卡腕問題與基礎(chǔ)研究的新成果密切相關(guān)。 這涉及到如何將這項新成果快速轉(zhuǎn)化為高端技術(shù)。 我們在這方面還是有分歧的,就是說從基礎(chǔ)研究的突破到技術(shù)換代的突破還是很少的。 有人說基礎(chǔ)研究沒有秘密,論文發(fā)表了。 但是,從論文的發(fā)表到技術(shù)的產(chǎn)生,誰先做到,誰就最快的產(chǎn)生出技術(shù),然后他就可以申請專利來堵住后來者。
因此,解決卡腕問題,以需求為導(dǎo)向的基礎(chǔ)研究和基礎(chǔ)研究的快速轉(zhuǎn)化非常重要。
《知識分子》:有人認為中國應(yīng)該摒棄幻想,建立獨立于英國的制度; 有人認為,中國不應(yīng)脫離全球化趨勢,而應(yīng)繼續(xù)加強開放合作,融入全球創(chuàng)新產(chǎn)業(yè)鏈。 您如何看待這兩種觀點?
楊偉:這個不能一概而論。 一方面,中國不可能什么都造自己的一套; 另一方面,如果有些東西還堵著,那就只能自己做一套了。
比如我們國家的民航和航天,民航一開始總想買,但是沒有發(fā)展。 最后買到一定程度就不會借給你了。 就航天而言,雖然不是最厲害的,但也還可以。 后來民航開始自己做,現(xiàn)在逐漸上來了。
但是有些東西還是配合比較好,因為按照經(jīng)濟學(xué)的理論,如果我們能在全球分工的產(chǎn)業(yè)鏈上不斷往上爬,在沒有障礙的情況下往上爬,這是最有效率的.
讓我給你一個反例。 本世紀(jì)初,曾有關(guān)于我國是否應(yīng)該制定新的中長期科學(xué)發(fā)展規(guī)劃的爭論,比如是否需要實施重大科技專項等。 國務(wù)院邀請一批經(jīng)濟學(xué)家。 從經(jīng)濟學(xué)的角度來看,經(jīng)濟學(xué)家說,如果你研究這個東西,還不如介紹這個,然后自己去做,這樣會省錢。 科學(xué)家居然不干了,說這不行,得自己干。 雙方爭論了很多,最后國務(wù)院決定照做。
現(xiàn)在看看那些國家重大項目,直接產(chǎn)生多少經(jīng)濟效益,你說不準(zhǔn)。 而且總的來說,如果沒有國家大項目和日本的一張牌,我們或許可以打全場。 有基礎(chǔ)就好。
所以,重要的東西,可以控制很多技術(shù)發(fā)展的高端領(lǐng)域光現(xiàn)象科技小論文初二,應(yīng)該自己去開發(fā),因為中國是一個大國。
對比中國的制造業(yè),我們先是產(chǎn)生了一個完整的工業(yè)體系,然后2010年左右我國制造業(yè)的還原值就超過了日本。對比看中國的科學(xué),我們現(xiàn)在基本已經(jīng)產(chǎn)生了一個完整的學(xué)科體系,雖然有幾個學(xué)科不是很好; 我們的學(xué)術(shù)產(chǎn)出可能在2020年超過日本。中國基礎(chǔ)研究的崛起比中國制造業(yè)的崛起落后六年。 應(yīng)該看到,中國還不是制造大國; 因此,到2030年,中國還達不到基礎(chǔ)研究強國的高度。 我們希望中國到2050年實現(xiàn)基礎(chǔ)研究強國的夢想。
印版編輯器 | 皮皮魚
更多精彩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