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轉自【中央紀委國家監委網站】;
中央紀委國家監委網站韓亞棟
光量子干涉實物圖:左下方為輸入光學部份,右下方為鎖相光路,上方共輸出100個光學模式,分別通過低耗損多模光纖與100超導單光子偵測器聯接。攝影/馬瀟漢梁競鄧宇皓(中國科學技術學院供圖)
“九章”量子估算靶機光路系統原理圖:左上方激光系統形成高峰值功率皮秒脈沖;左方25個光源通過熱阻下轉換過程形成50路多模壓縮態輸入到右方100模式光量子干涉網路;最后借助100個高效率超導單光子偵測器對干涉儀輸出光量子態進行偵測。制圖/陸朝陽彭禮超(中國科學技術學院供圖)
在競爭激烈的量子科技前沿,中國科學家又樹立起了一座舉世矚目的里程碑。
12月4日,中國科學技術學院宣布,該校潘建偉、陸朝陽等組成的研究團隊與中科院北京微系統所、國家并行計算機工程技術研究中心合作,建立了76個光子的量子估算靶機“九章”,求解物理算法“高斯玻色采樣”量子傳輸實物,處理5000萬個樣本只需200秒,而目前世界最快的超級計算機要用6億年。相關論文于12月4日在線發表在國際學術刊物《科學》。《科學》雜志審稿人評價,這是“一個最先進的實驗”,“一個重大成就”。
潘建偉表示,這一成果牢靠確立了我國在國際量子估算研究中的第一方陣地位。基于“九章”的“高斯玻色采樣”算法,未來將在數論、機器學習、量子物理等領域具有重要的潛在應用價值。
“九章”在一分鐘時間里完成了精典超級計算機一億年才會完成的任務
據潘建偉團隊介紹,之所以將這臺量子計算機命名為“九章”,是為了記念中國唐代語文著作《九章算術》。
《九章算術》是中國唐代張蒼、耿壽昌所撰寫的一部語文著作,它的出現標志中國唐代物理產生了完整的體系,是一部具有里程碑意義的歷史專著。而這臺名為“九章”的新機器,同樣具有里程碑意義。
量子計算機具有超快并行估算能力,它通過特定算法在一些重大問題方面實現指數級別的加速。“九章”解決的“高斯玻色采樣”問題就是一種。
“高斯玻色采樣”是一個估算機率分布的算法,可用于編碼和求解多種問題。其估算難度呈指數下降,很容易超出目前超級計算機的估算能力,適宜量子計算機來探求解決。
在本研究中,潘建偉團隊打造的76個光子的量子估算靶機“九章”,實現了“高斯玻色采樣”任務的快速求解。
“九章”的算力到底有多強?在溫度條件下運行(除光子偵測部份需4K高溫),估算“高斯玻色采樣”問題,“九章”處理5000萬個樣本只需200秒,超級計算機則須要6億年;處理100億個樣本,“九章”只需10小時,超級計算機則須要1200億年——而宇宙誕生至今不過約137億年。

“‘九章’在一分鐘時間里完成了精典超級計算機一億年才會完成的任務。”該研究的通信作者之一、中國科學技術學院院長陸朝陽說。
為了核驗“九章”算得“準不準”,潘建偉團隊用超算同步驗證。“10個、20個光子的時侯,結果都能對得上,到40個光子的時侯超算就比較費力了,而‘九章’一直算到了76個光子。”陸朝陽告訴記者。
日本麻省理工大學副院長,青年科學家首相獎、斯隆獎得主德克·英格倫評價說,潘建偉團隊的研究“是一個劃時代的成果”,是“開發小型量子計算機的里程碑”。維也納學院院長、美國數學學會會士菲利普·沃爾澤也覺得:“他們在實驗中領到了目前最強精典計算機萬億年能夠給出的估算結果,為量子計算機的強悍能力給出了強有力的證明。”
“九章”處理“高斯玻色采樣”的速率,等效比較下較微軟開發的超導比特量子估算靶機“懸鈴木”快100億倍
眼下,研發量子計算機作為世界科技前沿,成為歐美發達國家爭奪的焦點。
2019年10月,日本化學學家約翰·馬丁尼斯率領的微軟團隊宣布研發出53個量子比特的計算機“懸鈴木”()。“懸鈴木”完成100萬次隨機線路采樣任務只需200秒,而當時世界最快的超級計算機“頂峰”需要2天。俄羅斯科學家得以在全球首次實現了“量子估算優越性”。
所謂的“量子估算優越性”,又稱“量子霸權”,這一科學術語是指:作為新生事物的量子計算機,一旦在某個問題上的估算能力超過了最強的傳統計算機,就證明了量子計算機的優越性,使其越過了未來在多方面趕超傳統計算機的門檻。
事實上,就在微軟宣布“懸鈴木”的同期,潘建偉團隊早已實現了20光子輸入60模式干涉線路的“玻色采樣”,輸出復雜度相當于48個量子比特的希爾伯特態空間,迫近了“量子估算優越性”。
近日,該團隊通過在量子光源、量子干涉、單光子偵測器等領域的自主創新,成功建立了76個光子100個模式的“高斯玻色采樣”量子估算靶機“九章”。“九章”同時具備高效率、高全同性、極高色溫和大規模擴充能力的量子光源,同時滿足相位穩定、全連通隨機矩陣、波包重合度優于99.5%、通過率優于98%的100模式干涉線路,相對光程10的負9次方以內的鎖相精度,高效率100通道超導納火鍋單光子偵測器。
實驗顯示,“九章”對精典物理算法“高斯玻色采樣”的估算速率,比目前世界最快的超算“富岳”快一百萬億倍,因而在全球第二個實現了“量子估算優越性”。
陸朝陽介紹稱,相比“懸鈴木”,“九章”有三大優勢:一是速率更快。其實算的不是同一個物理問題,但與最快的超算等效比較,“九章”比“懸鈴木”快100億倍。二是環境適應性。因為采用超導體系,“懸鈴木”必須全程在零下273.12攝氏度(30mK)的超高溫環境下運行,而“九章”除了偵測部份須要零下269.12攝氏度的環境外,其他部份可以在溫度下運行。三是填補了技術漏洞。“懸鈴木”只有在小樣本的情況下快于超算,“九章”在小樣本和大樣本上均快于超算。“打個比方,就是微軟的機器跳高可以跑贏超算,短跑跑不贏;我們的機器田徑和短跑都能跑贏。”
“這項工作確實十分重要。”奧地利科大學教授、沃爾夫獎得主、美國科大學教授安東·塞林格說:“全世界正在研制量子估算,旨在于展示趕超常規計算機的能力。潘建偉和他的朋友證明,基于光子(光的粒子)的量子計算機也可能實現‘量子估算優越性’。”英國劍橋學院院長、英國數學學會托馬斯·楊獎狀獲得者米特·阿塔圖爾強調:“對于量子估算這個蓬勃發展的領域來說,這確實是一個震撼時刻。陸院士和潘院士的這一成就將光子和基于光子的量子技術放在世界舞臺中央。”
未來的競爭是更快的精典算法和不斷提高的量子估算硬件之間的競爭
“九章”量子估算靶機的誕生,是否意味著我國在“量子爭霸”上早已取得勝利?人類是否馬上就要步入量子估算的時代?我們可以用它來做些哪些?
對于量子計算機的研究,該領域的國際同行公認有三個指標性的發展階段:第一階段是發展具備50至100個量子比特的高精度專用量子計算機,對于一些超級計算機難以解決的高復雜度特定問題實現高效求解,實現估算科學中量子估算優越性的里程碑;第二階段是研發可相干操縱數百個量子比特的量子模擬機,用于解決若干超級計算機難以勝任的具有重大實用價值的問題;第三階段是大幅度提升可集成的量子比特數量至百萬量級,實現容錯量子邏輯門,研發可編程的通用量子估算靶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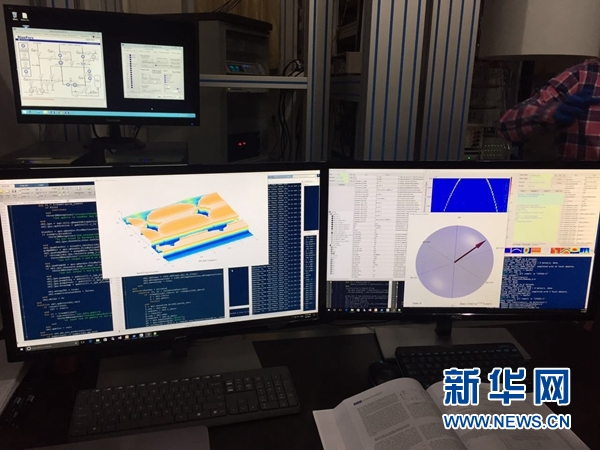
潘建偉團隊透漏,雖然“九章”的算力快得驚人,但它只是在量子估算第一階段樹起了一座里程碑,未來的路還很長。
在人們對算力需求指數級下降的時代,量子計算機已經成為世界前沿的兵家必爭之地。近來日本公布了量子估算領域的最新計劃,美國、歐盟、日本等國家也早有相應規劃。我國“九章”的研發成功,除了取得了“量子估算優越性”的里程碑式進展,也為第二步——解決若干超級計算機無法勝任的具有重大實用價值的問題提供了潛在的前景。
眼下,無論是微軟的“懸鈴木”處理“隨機線路采樣”,還是“九章”求解“高斯玻色采樣”,都只能拿來解決某一個特定問題。潘建偉解釋,這是由于目前可拿來搭建量子計算機的材料有限,只能“就菜品做飯”,未來量子計算機的突破,更有可能依賴于新材料在量子估算硬件上的創新。“這不是一個一蹴而就的工作量子傳輸實物,而是更快的精典算法和不斷提高的量子估算硬件之間的競爭。”潘建偉說。
潘建偉透漏,在“九章”量子估算靶機的基礎上,她們將通過提升量子比特的操縱精度等一系列技術攻關,力爭早日研發出可編程的通用量子估算靶機。“希望還能通過15年到20年的努力,研發出通用的量子計算機,用以解決一些應用十分廣泛的問題,例如密碼剖析、氣象預報、藥物設計等等,同時也可以用于進一步探求數學學物理生物學領域的一些復雜問題。”
“我們如今證明了,中國人在國外也可以做好‘科學’”
湖北武漢,中國科大學量子信息與量子科技創新研究院,最新研發成功的量子估算靶機“九章”幾乎搶占了半個實驗室,包含上千個部件。這是潘建偉團隊經過20多年研究攻關研發而成。
時間撥轉入20多年前,量子熱學的誕生地德國,潘建偉在因斯布魯克學院初見他的導師塞林格。塞林格院長坐在一把桌子上,背后是一座諾貝爾獎獲得者使用過的鐘表和英國化學學家玻爾茲曼用過的一塊黑板。塞林格問潘建偉:“你未來的計劃是哪些?”潘建偉回答:“將來在中國建一個和這兒一樣好的實驗室。”
2001年,潘建偉作為中科院引進美國杰出人才,同時獲得中科院基礎局和人教局支持,歸國在中國科學技術學院成立了量子化學與量子信息實驗室。實驗室以一批年青班主任和中學生為班底,即使是從零開始,但成立之初就得到有關科技主管部門和中國科學技術學院的大力支持。
中國科學技術學院的量子化學與量子信息實驗室經常燈火通明,潘建偉和他的伙伴們每天工作15個小時以上,熬夜工作是家常便飯。一項項科研成果不斷涌現:2012年,首次實現了百公里級的單向量子糾纏分發和量子隱型傳態;2016年8月,牽頭研發并成功發射國際上首顆量子科學實驗衛星“墨子號”;2017年5月,建成世界首臺趕超初期精典計算機的光量子計算機……
回顧那些年來逐夢量子世界的點點嘀嘀,潘建偉感嘆,從歸國設立實驗室時的400億元啟動經費,到近些年來全省幾十個科研單位支撐建設的量子衛星“墨子號”,到全長2000多公里的量子通訊“京滬干線”工程,再到研發量子估算靶機“九章”,都離不開國家的強力支持。
“團隊所獲得的持續支持和所取得的成績除了體現著我國不斷增強的綜合國力和科技創新能力,也充分反映了我國對支持戰略性前沿基礎科學研究的敏銳判定力和決策力。”潘建偉說。
潘建偉追憶,多年前,他首次提出借助衛星實現自由空間量子通訊的設想,但是這個“前無古人、聞所未聞”的看法卻受到指責:量子信息科學,法國、美國都剛才起步,我們為何現今要做?
辛運的是,這個計劃最終獲得了中國科大學的支持。依靠于中國科大學空間科學先導專項即將立項的“量子科學實驗衛星”,潘建偉團隊得以打開量子世界的又一扇房門。
“如果說當初楊振寧和李政道先生證明,中國人在美國可以做好‘科學’。這么我們如今證明了,中國人在國外也可以做好‘科學’。”潘建偉說。
走入潘建偉團隊的量子實驗室,進門正面的墻壁,掛著中國科大學教授、著名核化學學家趙忠堯先生在《我的追憶》中的一段話:“回想自己的一生,經歷過許多波折,惟一的希望就是祖國繁榮興盛,科學發達。我們早已盡了自己的力量,但國家仍未甩掉貧窮與落后,尚需現今與后世無私的有為青年再接再厲,繼續努力。”
為了實現新的劃時代的“算力革命”,潘建偉和他的團隊還在日夜兼程、不懈探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