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7年,赫茲通過高頻振蕩電路(LC電路)否定了電磁波的存在。 落回接收器上的藍色火花導致完美麥克斯韋理論的預言被否定,從此打開了一扇新的數學大門。
赫茲否認了電磁波的存在,也否認了光雖然是一種電磁波,(的確,兩者都具有波的性質)。 因此,早在17世紀,人們就光是波還是粒子展開了一場大辯論。 其實,還會有一些小插曲,眾所周知的牛頓和胡克就在這場大戰中。 一開始,“粒子論”和“波論”試圖取長補短,相得益彰,但遲早發現對方根本就是宿敵。 熱心人士發展了以胡克為代表的波動理論,以惠根斯的波動理論《光學》為論據,輔之以“牛頓環”和雙折射現象,使波動理論達到了一個新的高峰。 (波動理論有一個可怕的漏洞,以太,下面會解釋。) 然而,波動理論的領導者惹惱了歷史上最偉大的化學家。 牛頓,初升的太陽,本來是和粒子一起在波沙的,但是他和胡克的私人恩怨,促使他最終堅定不移地站在了粒子的陣營。 17、18世紀的牛頓體系高貴得讓人膽敢畏懼。 《粒子論》雖然理論牢不可破:這個巨人從粒子的角度解釋了色散和牛頓環,還有幾乎可以與《原理》媲美的《光學》……這些都是制約科學進步的巨石波浪理論。 這也結束了人類歷史上第一次關于光是波還是粒子的爭論。 隨著牛頓的加入,一切都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
幸運的是,一個世紀后,來自美國的托馬斯·揚再次開啟了這場對決。 一個非常叛逆精神的年輕人很少出現在信徒的家庭中。 通過研究人耳的結構,他接觸到光的一些問題,最后得出光是波的觀點。 1801年和1803年,他分別發表了論文報告,討論了如何解決牛頓環和繞射等光漲落問題,甚至粗略估計了光的波長。 事實上,粒子科學家已經舉出很多反例來批判,比如最著名的馬呂斯偏振光問題,但正如楊所說:“……你的實驗只能證明我的理論有缺點,但沒辦法證明解決它。證明他是假的。” 決定性的時刻出現在 1819 年,涉及光的衍射效應和光穿過物體時的運動。 本來,這是一個證明微粒至上的問題。 在菲涅爾嚴密的物理推理下,非常完美地解釋了光的衍射。 當泊松光斑出現在眾人面前時,所有人都驚呆了。 同時,《關于偏振光的相互作用問題》用剪切波理論解釋了偏振光現象,攻破了粒子理論的最后堡壘。 更可喜的是,麥克斯韋理論預言光雖然是一種電磁波,但偉大的麥克斯韋發表的三篇電磁理論論文具有劃時代的意義。 這第二場對決,對于起伏來說是一場大勝,他登上了化學第一的寶座。
好吧,雖然一切都結束了,雖然從那天起化學就完美無缺了,但是在熱力學方面,牛頓體系經過時間的洗禮已經顯示出它的偉大,一切都順其自然,海王星的發現更是火熱。 有了筆墨的加入,力學也建立了自己的熱力學三大定理,最難攻克的光學也以波結束了。 經典熱力學、經典電動力學、經典熱力學相輔相成,共同創造一個世界。 偉大的數學殿堂。 那么,這平淡背后隱藏著一個恐怖,讓我們回到第二段,我們有一個更重要的問題,這個問題就像1+1=2,人類需要空氣來呼吸,但它是最尖銳的波浪理論留下的問題——“以太”……
什么是“以太”? 你可能在日常生活中隱約看到過它。 是一種只能出現在游戲中的高頻詞匯。 “以太”究竟是什么東西,“肯定”是一種介質,而光速是30萬公里/秒,“以太”的強度肯定是非常大的。 然而事實是,沒有人能感覺到他的存在,就像隱藏在公式中的幽靈,極其堅硬的以太可以承載光速,卻連塵埃都無法移動。 當你打開圖書館搜索以太時,筆記本會顯示以太是古埃及哲學家設想的一種物質,是一種假想的電磁波傳播介質,被認為是無處不在的。 麻煩了,波浪理論再完美不過,他們竟然連自己原來的理論基礎都否定不了。 (簡單點說,古埃及的學者覺得有比四元素更純粹的存在,所以用在化學上,成為化學的基礎,用來代表光介質和絕對參照系。當他拋棄了榮耀,雖然當你想換臉賦予新的意義時,它還是被拋棄了,甚至成為偽科學的代名詞。)
毫不奇怪,我們現在的數學應該沒有那么復雜,我們可能還在為前人的優點沾沾自喜:看,我們人類多聰明啊。 然而,突如其來的新發現——邁克爾遜-莫雷實驗和松提輻射實驗卻讓人們大吃一驚。 簡單來說,邁克爾遜-莫雷的實驗就是檢測以太的光速,這意味著這可能是當時最精密的實驗,但結果卻令人心碎。 這個失敗的實驗意味著整個經典化學世界的崩潰,也引發了相對論革命的爆發。 另一個宋式實驗最終導致了量子理論。 革命爆發。
我們知道白色的物體是吸收了黑色的光波造成的,所以如果一束光射到物體上卻沒有反射,它看起來絕對是藍色的。 這也證明了輻射能量、頻率和濕度之間存在某種函數關系。 然而,可怕的是,通過科學家的計算,分別從波和粒子的兩個方向出發,得出兩個不相干的公式——維恩定理和瑞利-金斯公式,兩者是完全相反的,但都有一定的折舊程度(維恩公式適用于長波,瑞利-金斯公式適用于短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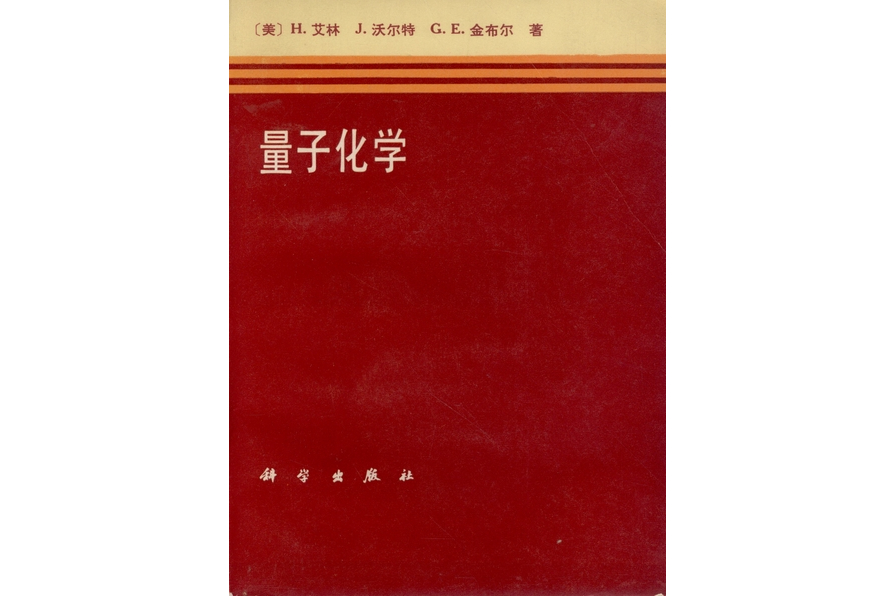
奇怪,其實人們也很疑惑,就在人們吐槽的時候,馬克斯·普朗克走上了歷史的舞臺。 作為量子科學的奠基人,我覺得有必要介紹一下:馬克斯·普朗克,日本化學家,出生于西班牙基爾,他的父親艾瑪·帕齊格(他父母的第二任丈夫,普朗克度過了最初的幾年他在基爾度過了多年的童年,直到1867年全家搬到蘇黎世,他就讀于蘇黎世的馬克西米利安文理學院,他的同事奧斯卡·馮·穆勒后來成為法國博物館的創始人。1990年12月14日,普朗克在美國數學會上報告了他的學術成果,成為量子理論誕生和新數學革命開始的偉大時刻,普朗克也因為這一發現獲得了1918年的諾貝爾化學獎。
好吧,言歸正傳,兩組公式只能在一個方面起作用。 他的任務是找到一個萬能公式,一個相當復雜的代數公式,可以用來正確勾勒出宋代輻射,以至于這個代數公式為了完美地總結實驗數據,在今天的理論化學中仍然經常被使用. 他無意間得出了一個可以演化成長波或退化成長波的公式,而這個公式就是普朗克宋體公式。 其實他也明白,配方的成功絕非僥幸,背后一定隱藏著更大的秘密。 問題是:公認的數學定理暗示了一個完全不同的公式。 正如普朗克所說:“, zu,, der, 。” 翻譯成英文,意思是:“我不期望發現一個新的臺灣,但我只希望了解已經存在的化學基礎量子物理的應用范圍,實際上可以加深。”
普朗克對這個問題深思熟慮,最終提出了一個全新的理論:輻射能只能以普朗克稱之為量子的基本單位的整數倍輻射。 根據普朗克理論,光量子的大小取決于光的頻率(即顏色),并且與一個數學量成反比。 普朗克將這個量縮寫為 h,現在稱為普朗克常數。 普朗克的假說與當時流行的數學概念完全相反,但他卻利用這個假說從理論上推導出了正確的Arial輻射公式。 普朗克的假設是徹底革命性的。 因此,如果不是因為他作為堅定保守的化學家的聲譽,他的假設無疑會被視為荒謬的想法而被駁回。 事實上,這個假設聽起來很奇怪,而且在這些特殊情況下它導出了正確的公式。 當時的大多數化學家(包括普朗克本人)都覺得這個假說不過是一個適用范圍狹窄的物理假設。 幾年后,普朗克的概念被證明可以應用于 Arial 輻射以外的許多不同種類的化學現象。
普朗克新理論的提出,導致大部分數學乃至整個物理學遭到破壞,急需重建。 一個新的時代從此拉開序幕。 量子理論就像一位突然出現的君主,打破了所有陳舊的微觀化學秩序,如閃電般劃破黑夜:E=h·v。 普朗克用這個公式,讓1900年12月14日成為量子的生日,普朗克也成為公認的量子科學教父。
但事實上,量子科學注定命運多舛。 它不像牛頓體系那樣精心建立,甚至它的母親普朗克也曾在量子科學和麥克斯韋理論之間徘徊。 量子就像一個怪胎,或者一個可憐的嬰兒。 創之者避而遠之,欲采之者亦懼而避之。 天哪,這是什么怪胎。
普朗克是個守舊的科學家,連他自己都不愿意承認量子假設是真實的數學事實。 如果把能量量子化,首當其沖的就是麥克斯韋理論。 人們在使用普朗克公式時,就像古人使用火一樣,充滿敬畏和不安,猶如上天賜予的禮物。 直到1905年,愛因斯坦在德國波恩專利局將人們從光電效應中解放出來——光子(即1962年被劉易斯取代的光子),才讓人們有了一點線索。
我們已經知道,光是一種波動,波的硬度代表了它的強弱。 電子被囚禁在金屬內部。 如果外部能量不夠,電子很難被打下來。 但是,如果波的硬度降低,如果頻率不夠,電子也無法被擊落,也就是說:光的頻率決定了它能否從金屬表面被擊落,而光的硬度光決定了被擊出的電子數。 讓我們回到公式:E=hv,什么意思? 愛因斯坦抓住了問題的關鍵,頻率和能量。 提高頻率只是提高了單個量子的能量,而光的硬度,只是減少了量子的數量。
問題兜了一圈又回到了起點,光的本質是什么。
愛因斯坦提出了光以量子方式吸收能量的跨時代假說,很難間斷地積累。
直到后來,康普頓在研究被電子散射的X射線時,發現了一個奇怪的現象。 散射的X射線實際上分為兩部分,一部分與原來的波長相同,另一部分則比原來的波長長。 更進一步,他推導出波長變化與散射角的關系,實驗清楚地告訴人們,輻射量子除了能量之外,還有一定的沖量。
1911年秋天,一個名叫索爾維的人做了一件了不起的事。 他慷慨地贊助了一次全球科學會議。 而這次會議,著名的索爾維會議,聚集了二十四位世界上最杰出的科學家,在歷史上留下了光輝的一頁。
新的篇章被玻爾揭開量子物理的應用范圍,巴爾莫公式讓玻爾眼前一亮,他看到了新的曙光——經典理論中的連續性被破壞,量子化條件必須成為原子理論的主人! (后來經過多年摸索,他的《論原子分子結構》、《單原子核體系》、《多原子核體系》構成了量子化學的三大巨著)我覺得我必須重寫這些話再說一遍:必須假設能量在發射和吸收時必須分成幾部分。 其實你不太明白我為什么非要解釋這句極其簡單的句子。 恐怕你會告訴我這之間有什么關系,有什么意義。 好吧,仔細聽,這些想法與你在中學認識的大多數化學家的想法詭異地相反,截然相反,甚至可以徹底摧毀一個人的世界觀! 簡單列舉幾個反例:你能相信3點到4點之間沒有3點30分這樣的時刻嗎,你能相信冰在沸騰過程中沒有經歷50攝氏度嗎? .. 是不是很有趣? 更有趣的是古埃及的埃利亞學派,為了驗證自己的理論——世界上只有一個且唯一的存在(即沒有運動),學校老師隱瞞悖論提出的口才——芝諾追烏龜悖論,那只阿喀琉斯永遠追不上的兔子告訴人們:量子效應阻止了時間和空間的無限細分。
隨著時間的進步,量子科學也在不斷發展,舊的量子理論也在不斷被打破,由此衍生出的推論(如泡利原理、洪德法則等中學物理學生一頭霧水的)將使人類的理論結構 從宇宙論到主體,分為廣義相對論和量子場論,最后歸類為一個哲學體系。 量子理論革命的破壞力是驚人的。 概率解釋、互補性原理和不確定性原理這三個核心原理破壞了經典世界的(嚴格)因果性和(絕對)客觀性。 新的量子解釋 一個全新的世界,甚至違背人們的理性。 但這有什么關系呢? 一個全新的時代就這樣呈現在了人們的面前。
化學是萬物的原理,量子科學只是它的三個小分支。 世界的奧秘還有待你去發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