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海時間10月4日17時45分,諾貝爾獎委員會公布了2022年數學學獎獲得者:阿蘭·阿斯佩、約翰·克勞澤和安東·塞林格,以嘉獎她們在“糾纏光子實驗、確立對貝爾不方程的違背和開創性的量子信息科學”方面的成就。
2022諾貝爾化學學獎獲得者:阿蘭·阿斯佩、約翰·克勞澤和安東·塞林格
諾貝爾化學學委員會強調,她們的工作“為量子技術的新時代奠定了基礎”。委員會成員伊娃·奧爾森說,量子信息科學在安全信息傳輸和量子估算等領域具有廣泛的影響,是一個“充滿活力且發展迅速”的領域。
證明愛因斯坦錯誤
“他們三位得獎是實至名歸。”圖靈量子創始人、上海師大集成量子信息技術研究中心所長金賢敏對《中國新聞周刊》說。他解釋,阿斯佩等五人是量子信息領域公認的開創者和先驅,這種實驗結束了愛因斯坦和舊量子論奠基人、丹麥化學學家尼爾斯·玻爾持續近百年的爭辯。
20世紀20年代的量子熱學革命就是在這場爭辯中開啟。量子熱學常年以來的核心理論困局是“遠距離的幽靈行動”問題,即為什么兩個或多個粒子以所謂的糾纏態存在,更進一步闡明,糾纏對中的一個粒子發生的事情,就決定了另一個粒子發生的事情——即便它們相距很遙遠。例如,一個光子的偏振光態是“向上”的,另一個光子的偏振光態就必然是“向下”的,如同“心靈感應”。對此,愛因斯坦覺得,糾纏對中的粒子包含了隱藏變量,即局部因果關系,因而量子熱學方式是不完整的。其實,愛因斯坦不相信上帝會擲色子,玻爾則強烈反對這一推論。
1935年,愛因斯坦等更進一步提出了知名的EPR佯謬,核心觀點是:量子熱學沒有提供對現實完整描述。1964年,在法國核子研究中心工作的德國化學學家約翰·貝爾提出了知名的貝爾不方程,這一不方程的核心在于,假如存在隱藏變量,則大量粒子檢測結果間相關性永遠不會超過某個值。倘若能通過實驗驗證,檢測結果違背了貝爾不方程,就意味著量子熱學不能用局域隱變量理論來解釋,即證明愛因斯坦的認知是錯誤的。
后來事實表明,阿斯佩、克勞澤和塞林格都通過實驗驗證了違背貝爾不方程的情況,因而,兩人早在2010年就共同獲得了世界數學學界最高成就獎之一的沃爾夫獎,得獎理由是“他們對量子化學學基本概念和實驗的貢獻,非常是對貝爾不方程一系列愈加復雜的測試或使用糾纏量子態對其擴充。”
克勞澤是世界上第一個對貝爾不方程驗證的科學家,他去年早已80歲了。1972年,正在加洲學院伯克利校區任職的他就與博士生斯圖爾特完成了世界上首次對違背貝爾不方程的實驗觀察。在哥大讀書期間物理量子力學,克勞澤的量子熱學課還曾連續兩次獲得C,又被迫重修了兩次。
這類初期實驗常常存在漏洞。1982年,還在讀博的阿斯佩改進了克勞澤的實驗,第一次真正意義上補上了漏洞,驗證了貝爾不方程并不創立。阿斯佩1947年出生在美國,先后在德意志大學和倫敦高等師范大學等任職,后來成為了美國國家科學研究中心的杰出名譽科學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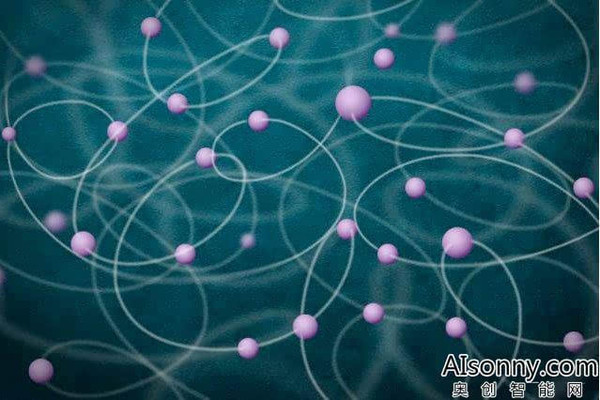
中國科大學教授、中國科大學量子信息重點實驗室處長郭光燦對《中國新聞周刊》分析說,貝爾不方程是量子熱學發展中一個十分重要的理論,這個理論之所以這么重要,是由于它對“量子熱學是否正確”這樣的重大問題作出了一個判別。而在驗證的所有實驗中,阿斯佩實驗又是其中最重要的一個,由于初期實驗漏洞太多,并不令人信服,但阿斯佩實驗第一次“用光學的方式真正把道理講清楚”,被學界所公認。實驗提供了一個十分明晰的結果:量子熱學是正確的,沒有隱藏的變量,“幽靈肯定存在”。
“我1990年代到阿斯佩的實驗室視察時遇見了他,他是個做學問很認真的人,他當時自己說,他的實驗仍有漏洞,但這并不影響實驗的推論。”郭光燦說。
實驗的漏洞被完全“堵上”要等到2015年,這是塞林格的工作。在一系列實驗中,他使用了距離源足夠遠、快速可切換的偏振光器,還使用大概600年前星體發出的光來進行測試,以盡可能降低“歷史性”中的隱藏變量。包括塞林格在內的多個團隊完成了“無漏洞”的貝爾不方程驗證。
塞林格1945年出生于荷蘭,1971年在維也納學院獲得博士學位,1999年加入維也納學院任教,后來成為法國科大學校長。值得一提的是,國外著名量子通訊專家潘建偉1996年在德國攻讀博士學位時,就師從塞林格。如今,塞林格團隊與中國科大學合作密切,參與了中科院主導的洲際量子通訊實驗,在國際上首次實現深圳--維也納兩地量子保密通訊。
諾貝爾化學學委員會主席安德斯·伊爾貝克在頒獎時說,三位得獎者各自使用“兩個粒子雖然在分離時也表現得像一個單元”的糾纏量子態,進行了開創性實驗,實驗結果為基于量子信息的新技術掃清了障礙。“對糾纏態的研究十分重要,甚至趕超了解釋量子熱學的基本問題”。
《星際迷航》中的“超時空傳輸”
這種開創性實驗的重要意義,除了重新確認了量子熱學糾纏態存在的基礎理論,并且開啟了第二次量子革命——量子通訊技術誕生。
2022年諾貝爾化學學獎的公布現場,潘建偉團隊的“墨子號”也公開“亮相”,出現在介紹得獎者成果的案例展示中。2016年8月16日,中國發射了全球首顆量子科學實驗衛星“墨子號”,于2017年1月18日即將舉辦科學實驗,打造“墨子號”的基礎科學原理,就是塞林格團隊1997年首次完成的量子隱型傳態實驗。“這可能是頒獎給塞林格的重要理由之一。”郭光燦解釋道。
哪些是量子隱型傳態?
簡單來說,就是《星際迷航》中的超時空傳輸,即點對點的遠距離“傳送”,量子隱型傳態就是借助糾纏態傳輸量子信息。但值得注意的是,在這個過程中,傳輸的是兩個糾纏粒子的狀態,例如載流子狀態,而非粒子本身,例如把粒子A的未知量子態傳輸給遠處的另一個粒子B,讓B粒子的狀態弄成A粒子最初的狀態。
金賢敏解釋說,當實驗人員想傳輸一個量子態時,先把這個初始量子態和量子糾纏對中其中一個粒子“碰一下”,“進行一系列操作”,再把操作結果發到糾纏對的另外一個粒子處,對其進行一定操縱和旋旋之后,“另外一個粒子都會和最初想傳輸的量子態一模一樣,也就是通過糾纏做一個橋梁,可以傳遞任意未知的量子態。”
1997年,塞林格首次在實驗中成功傳送了一個光子的載流子,相關成果于當初12月被發表在《自然》上,題為《實驗量子隱型傳態》。論文強調,量子隱型傳態是量子系統狀態在任意距離上的傳輸和重建,也是量子估算網路的關鍵組成部份。幾年后,塞林格團隊又成功將秘密信息編碼成糾纏光子串,使監聽者未能有效攔截那些信息。
在《實驗量子隱型傳態》一文中,27歲的潘建偉擔綱第二作者,該文后來還入圍了《自然》的“物理學百年21篇精典論文”。“入選的那些論文中,后面20篇都領到諾獎了,這是第21篇,明年也獲得了諾獎。”金賢敏說。金賢敏是潘建偉的中學生,在博士求學期間,就在野外環境下舉辦了三年量子隱型傳態實驗。
郭光燦覺得,這項工作的重要意義,在于首次實現了對粒子的“操縱”,而這是量子通訊的基礎性工作。諾貝爾化學學委員會在頒獎時也說:“能夠操縱和管理量子態及其所有屬性層,使我們才能獲得有著意想不到潛力的工具。”
潘建偉10月4日接受《知識分子》采訪時對塞林格的工作進行了總結:“他的工作直接促使了量子信息領域的發展,相當于起到了從量子基礎到量子信息領域的橋梁作用。”金賢敏強調,這些“量子態級別的高精度大規模操縱”,促使了以量子估算、量子通訊、量子精密檢測和量子成像為代表的一系列新技術的崛起。
目前,量子通訊是惟一被證明無條件安全的通信形式;量子估算則有著遠超傳統計算機的超快的并行估算能力。
如今,中國在量子通訊技術上早已處于全球前列。2009年,潘建偉團隊與復旦學院合作,在廣州古北口與湖南永清之間實現了16公里的量子態隱型傳態,相當于此前世界紀錄27倍。2015年,潘建偉團隊進一步實現了單光子多自由度的量子隱型傳態,首次證明了一個粒子的所有性質在原理上都是可以被傳輸的,即完整意義上的量子隱型傳態。去年5月,潘建偉團隊借助“墨子號”首次實現了月球上相距1200公里兩個地面站之間的量子態遠程傳輸,向建立全球化量子信息處理和量子通訊網路又邁出了重要一步。
與此同時,全球各國都在占領“量子賽道”。日本正在建造量子衛星鏈路,特朗普政府2018年啟動了德國量子行動計劃,計劃在2019~2023年在量子研究方面投入12.75億澳元。2018年10月,歐共體也宣布了《量子旗艦計劃》,計劃在未來六年間在量子傳感、量子通訊與量子計算機領域投入10億英鎊。英國宣布了一項規模高達18億美元的量子技術兩年投資計劃。獲悉,中國量子國家實驗室投入規模預計在未來5~10年達到數百萬元人民幣。下一步,中國量子通訊技術發展將主要聚焦三個方向:量子通訊安全性定量化、量子通訊系統芯片化和大型化、完善量子網路建設的方法和合同的更新。
在量子信息技術中,多位業內人士對《中國新聞周刊》指出,量子精密檢測是最接近產業化與實用化的,通過量子態對外界進行檢測,在精度上突破了精典熱學的散粒噪音極限。潘建偉曾在接受《中國新聞周刊》采訪時也強調,量子精密檢測的用途很廣,包括時間、長度、溫度等尺度,他預計接出來的5到15年間,各色各樣的應用會相繼推出。
郭光燦表示,量子通訊“最大的益處”是可以把量子節點連結在一起,共同構成一個量子網路,可以和量子估算融合在一起,這將是未來“有很大發展的一個方向”,但在當下,我們仍處在對節點的研究過程中,而在應用層面,最有前景的則是量子計算機。潘建偉說,在兩年內,有信心能建造出“一些專用的量子模擬機來促進整個領域的發展”,而10~15年后通用的量子估算會取得長足進展。
那些都是在不遠的未來將要發生的事情。而在更遠的時間的盡頭,“生命、宇宙以及任何事情的終極答案”是哪些?
塞林格最喜歡的書是《銀河系漫游手冊》,這本書中有一臺強悍的超級計算機,對于上述問題,在經過歷時750萬年運算與驗證以后,超級計算機吐出的最終答案是“42”。作為一位狂熱的水手,塞林格將他的船也命名為“42”。他說:“如果我們真正去深入了解為何世界有量子熱學物理量子力學,即42的來源,我有一種覺得,我不相信量子熱學是最終定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