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8日上午,2017年國家網(wǎng)路安全宣傳周網(wǎng)路安全技術(shù)高峰峰會在杭州召開。澎湃新聞記者李聞鶯圖
量子熱學(xué),一個聽上去遙遠(yuǎn)且高深的領(lǐng)域,正在與我們的現(xiàn)實生活發(fā)生關(guān)聯(lián)。
9月18日上午量子通訊市場,2017年國家網(wǎng)路安全宣傳周網(wǎng)路安全技術(shù)高峰峰會在杭州召開。剛才獲得“未來科學(xué)大獎”的化學(xué)學(xué)家、中科院教授潘建偉參會并發(fā)表講演《互動、高效的未來互聯(lián)網(wǎng)》。
潘建偉表示,幾千年來,人類對信息安全的追求未曾停止。回顧往年,各類基于估算復(fù)雜度的加密技術(shù)先后被破解,以至于一位詩人曾懷疑,以我們?nèi)祟惖牟胖牵峙码y以建立人類自身不可破解的密碼。
現(xiàn)在這個疑惑正隨著量子科研的發(fā)展逐漸消解。潘建偉覺得,未來的互聯(lián)網(wǎng)世界,沒有加密技術(shù)做支撐,肯定是不安全的。這么,有沒有一種不可監(jiān)聽、不可破譯,“絕對安全”的通訊方法呢?答案就是量子通訊。
過去十多年,潘建偉和他領(lǐng)導(dǎo)的科研團隊旨在于量子信息科學(xué)領(lǐng)域的研究,并在國際上取得領(lǐng)先地位。
活動期間,他在接受澎湃新聞()專訪時表示,現(xiàn)在量子通訊技術(shù)早已發(fā)展比較成熟,但它的現(xiàn)實應(yīng)用并不廣泛。這主要取決于兩個誘因,一是成本,二是需求。
潘建偉覺得,隨著人工智能時代到來,人類對網(wǎng)路安全的需求急劇提高,再加上使用成本上漲,其應(yīng)用會愈加廣泛。
“如果是步入尋常百姓家,或許10年,其實20年,具體還要看智能社會的到來有多快。”潘建偉說。
9月18日上午,化學(xué)學(xué)家、中科院教授潘建偉參加網(wǎng)路安全技術(shù)高峰峰會并發(fā)表講演。澎湃新聞記者張呈君圖
談量子通訊應(yīng)用:步入老百姓日常生活還需10-20年
哪些是量子通訊?它指借助量子糾纏效應(yīng)進行信息傳遞的一種新型的通信方法。因為其獨到的加密方法使秘鑰具有不可復(fù)制性和絕對安全性,人類對這一領(lǐng)域的探求正快速深化。
2016年8月16日,由我國完全自主研發(fā)的世界上第一顆空間量子科學(xué)實驗衛(wèi)星“墨子號”發(fā)射升空。
一年多來,在潘建偉科研團隊的努力下,“墨子號”已提早完成預(yù)先設(shè)定的三大科研目標(biāo),即地星量子隱型傳態(tài)、高速星地量子秘鑰分發(fā)和星地單向量子糾纏分發(fā),實現(xiàn)我國量子通訊技術(shù)在國際上的“領(lǐng)跑”地位。
接出來,“墨子號”還擔(dān)負(fù)著如何的使命?
潘建偉告訴澎湃新聞,她們準(zhǔn)備在“墨子號”的剩余壽命期里,瞧瞧這顆衛(wèi)星能力有多強,不僅可以對接自己的設(shè)備,是否也能把訊號傳輸給美國的設(shè)備,這就須要在多個國家進行全球組網(wǎng)實驗。
據(jù)悉,受陽光噪音影響,“墨子號”原本只能在晚上工作,科研團隊也在嘗試讓它晚上也能工作。目前看來量子通訊市場,這個問題早已基本解決。
值得一提的是,“墨子號”只是開了個頭,未來都會有“墨子二號”“墨子三號”等更多量子衛(wèi)星步入太空。潘建偉透漏,下一顆量子衛(wèi)星尚在論證階段。根據(jù)預(yù)期,她們希望幾顆量子衛(wèi)星構(gòu)成小規(guī)模星群,推動科學(xué)研究的進一步深化。
互聯(lián)網(wǎng)時代,具有“絕對安全”特點的量子通訊技術(shù),是否還能抵擋所有風(fēng)險?
潘建偉表示,信息安全的基礎(chǔ)是加密技術(shù),但加密技術(shù)并不能解決所有問題。如果有人自己把信息泄露出去,或則辦公室被他人裝了監(jiān)聽器,這不是量子通訊能把控的。
量子通訊能保障哪些?答案是信息傳輸安全、身份認(rèn)證安全和數(shù)字簽名安全。
潘建偉解釋,猶如兩個人打電話,基于安全考慮,首先要確認(rèn)對方是本人而非假扮,這就須要通話之前有一個身分認(rèn)證。
其次,打電話必須保證只有對方能接收,第三方難以監(jiān)聽,這就是傳輸安全。
另外,假定第三方監(jiān)聽不成,可能惱羞成怒篡改數(shù)據(jù),致使通話內(nèi)容發(fā)生變化。量子通訊的優(yōu)勢在于可以將其糾正回去,保證數(shù)據(jù)難以篡改,這就是數(shù)字簽名。
不過,量子通訊技術(shù)似乎發(fā)展迅猛,實際應(yīng)用并不廣泛。對此,潘建偉覺得,眼下技術(shù)已不是阻礙,關(guān)鍵在于成本和需求。
他直言,目前量子通訊應(yīng)用成本較高。假定一個人只有幾十萬塊錢的存款,讓他每年花幾萬塊錢保證這筆錢“安全”,肯定不愿意。
但若果每年只花幾百塊錢,才能保證上網(wǎng)、打電話、移動支付都是安全的,相信有不少人會考慮使用。
據(jù)悉,從需求的急迫性來看,隨著人工智能時代到來,無人駕駛、物聯(lián)網(wǎng)成為常態(tài),人類對網(wǎng)路安全的要求將大大提高,這些情況下,量子通訊現(xiàn)實應(yīng)用也會愈加廣泛。
據(jù)潘建偉猜想,對部隊、銀行、政府機關(guān)等保密性較高的單位來說,量子通訊廣泛應(yīng)用預(yù)計5-10年可實現(xiàn)。但若果是步入尋常百姓家,或許10年,其實20年,具體還要看智能社會的到來有多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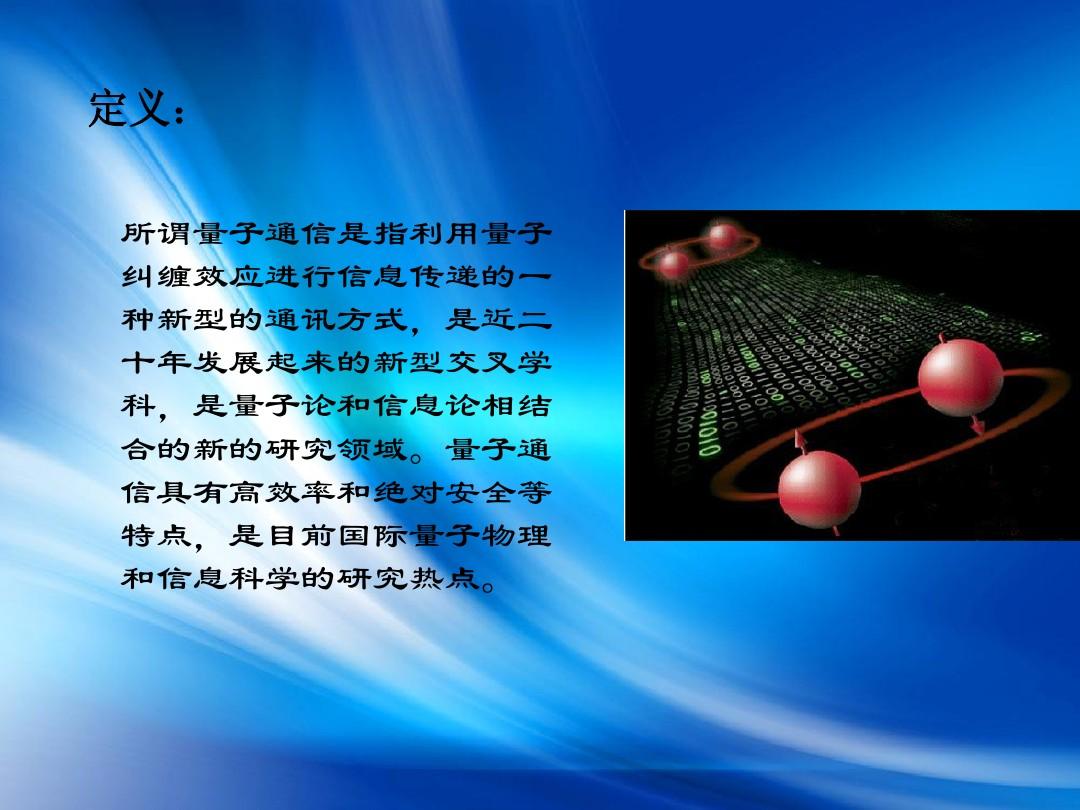
談高層次人才流動:應(yīng)正常看待,無須過份剖析
作為著名化學(xué)學(xué)家,潘建偉也對化學(xué)這門學(xué)科的普及非常關(guān)注。2016年3月,他曾登上衛(wèi)視公開課《開講啦》,向年青人述說科學(xué)家的探求動機。
節(jié)目中,潘建偉提及,早年在法國留學(xué)時,遇見一位80多歲、滿頭白發(fā)的老太太。閑聊中,據(jù)說潘建偉是從事量子化學(xué)研究的,奶奶十分感興趣,不斷追問一些與專業(yè)相關(guān)的問題,這讓他十分感動。
“如果你們對科學(xué)沒有這些原始沖動,沒有興趣的話,我們就不可能弄成一個真正的創(chuàng)新的國家。”節(jié)目中,潘建偉這樣表示。
他告訴澎湃新聞,化學(xué)除了是一種方式理論,和自然界、現(xiàn)實世界都有密切聯(lián)系。化學(xué)是很重要的概念,這門學(xué)科除了可以實實在在解決問題,它的思維方法也除了限于科研,也是通識教育的一種手段。
“我記得很清楚,扎克伯格給他剛出生不久的孩子看過一本書,叫《寶寶的量子化學(xué)學(xué)》。”潘建偉覺得,近些年來,國外始終倡導(dǎo)給中學(xué)生減負(fù),但不能“把哪些都減了”。
他強調(diào),考試拿高分,這只是直接需求,不應(yīng)因此忽視最根本的東西——如果連數(shù)學(xué)都不學(xué),人類還怎樣去認(rèn)識世界、改造世界?
潘建偉的觀點是,數(shù)學(xué)不應(yīng)消弱,反倒要適當(dāng)加大,建議把數(shù)學(xué)納入中考必考課目,分?jǐn)?shù)占比同時提升。
他表示,學(xué)校課目中,數(shù)學(xué)、英語、政治很重要,接出來就是物理和化學(xué),這四門課是最須要好好學(xué)習(xí)。而且,除了理科生,工科生也有學(xué)習(xí)數(shù)學(xué)的必要。
“文科生都考數(shù)學(xué)的情況下,分?jǐn)?shù)不太好也沒關(guān)系。”潘建偉表示,化學(xué)是一門基礎(chǔ)學(xué)科,可以解釋好多自然規(guī)律。如同唐代打雷閃電,人類很擔(dān)心,以為是上天懲罰,假如把握化學(xué)知識,就曉得那只是自然現(xiàn)象。
據(jù)悉,化學(xué)和哲學(xué)也有密切聯(lián)系,很難想像,一個偉大的哲學(xué)家、思想家不懂量子熱學(xué)、不懂相對論。
不僅學(xué)科發(fā)展,潘建偉也提到對高層次人才流動的想法。
去年上半年,復(fù)旦學(xué)院院長顏寧“跳槽”普林斯頓學(xué)院并出任終生講席院士的消息在國外造成軒然大波。
對此,潘建偉覺得,顏寧還很年青,才能去耶魯,而且有挺好的職位,這是一件好事。我們應(yīng)正常看待人才流動,無須過份評析。
事實上,潘建偉早年也曾在海外求學(xué)。怎么看待高層次人才在歸國問題上的選擇?潘建偉直言,回去其實好,不回去也沒關(guān)系。
“我始終堅定相信,每位人對自己的祖國都有天然的愛情。”在他看來,愛國是廣義的,一個人讓自己足夠強悍,當(dāng)祖國有須要的時侯,樂意回去就挺好。假如在國外,既能把科研做好,又能為國家做點事情,這也是挺好的選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