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華社安徽6月27日電(記者喻菲、徐海濤)“上帝是否擲色子”,這個困惑過愛因斯坦的量子化學核心奧秘同樣讓潘建偉經常凝心思考,在他眉目間刻出兩道深深的溝痕。
從潘建偉第一次認識到量子世界的吊詭詭異到沉溺其中不可自拔已過去20多年。為什么會有量子疊加、量子糾纏這種奇特的現象尚無答案,他卻仍然旨在于借助奇特的量子特點來制造不可破譯的密碼,發展保密通訊,研發強悍的量子計算機……
世界首顆量子衛星“墨子號”從太空構建了迄今最遙遠的量子糾纏,證明在1200多公里的尺度上,愛因斯坦都倍感匪夷所思的“遙遠地點間的奇特互動”依然存在。作為量子衛星首席科學家的潘建偉還有更大的目標——在地月間構建30萬公里的量子糾纏,檢驗量子化學的理論基礎,并探求引力與時空的結構。
在好多人眼中,潘建偉是傳奇:29歲,他參與的有關量子隱型傳態的研究成果,同倫琴發覺X射線、愛因斯坦構建相對論等影響世界的重大研究成果一起,被《自然》評為“百年化學學21篇精典論文”;31歲,任中國科學技術學院院長;41歲,成為中國當時最年青教授;45歲,獲國家自然科學銀獎……
得獎無數的他,卻說得獎是麻煩,易惹來責難。他是中國科學屋內的名星,是媒體追逐的對象,但他不想當名星,但求科學遭到國人關注。
緣起迷戀
潘建偉1970年3月生于湖北東陽,自小成績優秀。媽媽從不限制他,由他做感興趣的事。1987年,他考入中國科學技術學院近代化學系。他對學院生活最深的印象是,朋友間比著起床早睡學習,拚命喝酒通宵讀書。
2016年5月28日,在量子保密通訊廣州總控中心內,量子科學實驗衛星首席科學家潘建偉教授演示實用化量子通訊產品進行遠距離保密通話。新華社記者才揚攝
他的學院朋友,現在是暗物質衛星科學應用系統總師的伍健追憶,潘建偉是個很有意思的人。他給潘建偉剃過眉毛,有點像便器蓋,而且潘并不吵架。不僅學習,潘建偉也很會享受生活,有次和朋友挪到水閘摸了一盆子田螺回去,在寢室煮著吃。
1990年潘建偉第一次接觸量子熱學。那時他精典熱學、電動熱學、統計熱學都學得挺好,卻完全搞不明白量子熱學,有次期中考試量子熱學差點沒及格。
“雙縫實驗中,人沒有‘看’電午時,就不能說它是從哪條縫過去的,這實在太奇怪了,這不對啊。一個人要么在北京要么在上海,如何會同時既在北京又在上海呢?”量子世界的奇怪與陌生讓潘建偉深陷這樣的苦思。
如今回看,潘建偉覺得這是最好的現象,“量子熱學的創始人之一玻爾說,假如學了量子熱學后,你不認為奇怪,不認為不可思議,不犯糊涂的話,那你根本就沒學懂。”
量子世界越怪異,潘建偉越想搞明白。于是,他選擇與量子“糾纏”下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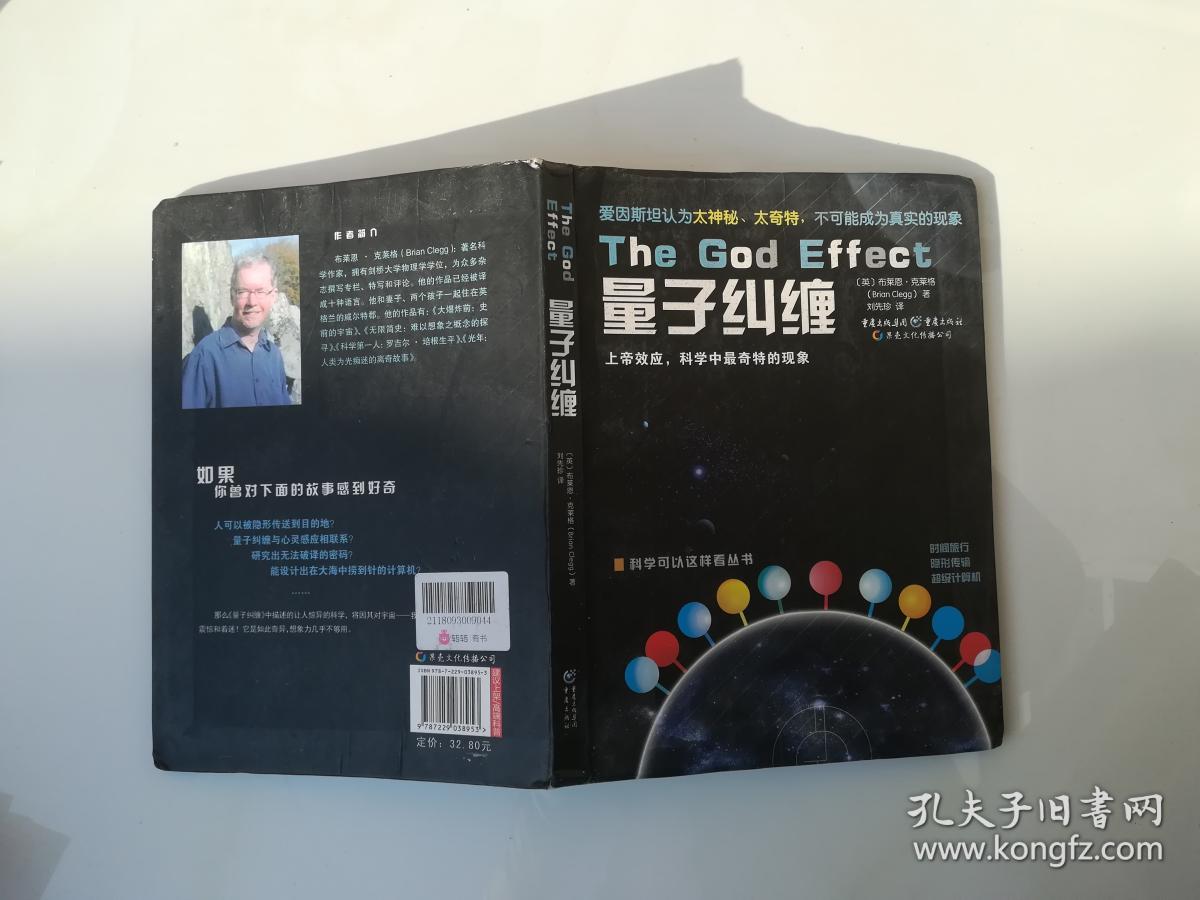
他認識到,化學學終究是門實驗科學,再奇妙的理論若得不到實驗檢驗,無異紙上談兵。但是,上世紀90年代中國缺少舉辦量子實驗的條件。1996年碩士結業后,潘建偉赴量子科研的重鎮——奧地利因斯布魯克學院攻讀博士學位,師從量子實驗研究的世界級大師塞林格。
一個理論化學專業的碩士,想要很快進入實驗量子化學前沿,其中困難可想而知。為早日把握要領,潘建偉幾乎整天泡在實驗室里。
塞林格在接受新華社記者專訪時說,潘建偉剛來讀博士時未曾做過實驗,但很有實驗的天賦。“我派他和一個團隊去做量子隱型傳態的實驗,那是十分復雜的實驗。他立刻就接受并投入其中,對實驗飽含熱情。過了一段時間,他就成為該項實驗的領軍人物。”
在老師眼中,當實驗中出現問題,潘建偉從不膽怯,把困難當作更下層樓的激勵,你們總是聽他說“情況挺好”,這個特別豁達的人,總能找到解決問題的辦法,你們都喜歡他。
“毫無疑惑,他如今是世界上這個領域最好的科學家,我十分為他驕傲。”塞林格說,“我也很鼓勵他歸國發展,這兒有挺好的機會。中國在量子通訊領域已步入世界先進行列,這兒有很大一部份是潘建偉努力的結果。”
做盤“量子好菜”
潘建偉把握了先進的量子技術后,急切地希望中國在信息技術領域捉住此次超越發達國家并把握主動權的機會。
1997年起,他每年暑假回到交大講學,為中國在量子信息領域的發展提出建議,推動研究人員步入該領域。2001年,他獲得中科院、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捐助,在交大成立了量子化學與量子信息實驗室。
量子信息研究集多學科于一體,要想突破,須擁有不同事科背景的人才。有一手好廚藝的潘建偉曉得,做盤好菜,須要各類各樣的好原料。
潘建偉將不同事科背景的年青人送出國門,到日本、英國、美國、瑞士、奧地利等國學習鍛練。就這樣潘建偉 量子通訊,他的團隊把握了國際上最好的冷原子技術,最好的精密檢測技術,最好的多光子糾纏操縱技術……
近些年,潘建偉團隊已在《自然》《科學》《物理評論快報》等國際重要學術期刊上發表論文約200篇,被廣泛引用。
科學帶來內心安寧
實驗中難免有讓人沮喪沮喪的時侯。但潘建偉說,做自己喜歡的事須要耐心,欲速則不達。“我樂意循序漸進地學習、工作。成功了,其實很高興;不成功,也不認為失落,就再來一次。關鍵是享受這個過程帶來的樂趣。”

“追求量子化學的奧妙,能讓人獲得內心的從容和安寧,就像陽光燦爛的夏天,走在青草地上般心情愉快。”他說。
潘建偉是愛因斯坦的崇敬者,學院時就喜讀《愛因斯坦選集》,“愛因斯坦的詩歌是最深刻、最美的,對于我,那就是天籟之音。”
“研究量子化學對我的性格、思想形成了影響。在牛頓熱學上面,0和1,黑或白,要么絕對正確,要么絕對錯誤。但量子熱學告訴我們,對錯、好壞是很難劃分的,這時人就顯得寬容。”
潘建偉在忙碌工作中出席了好多科普活動,還創立了以科普為目的的墨子沙龍。他說:“建設創新型國家潘建偉 量子通訊,必須培養公眾的科學興趣,提高公眾科學素質,否則就不可能建成真正創新的國家。”
摘取化學“皇冠上的明珠”
歲月飛逝。量子世界一如既往地詭異、難以飄忽。神奇的量子糾纏能在時空中無限延伸下去嗎?
“至少現今理論是這樣的,但其實量子糾纏會遭到引力影響,它的品質會升高。而通過不斷地擴充量子糾纏分發的距離,在實驗上找尋量子化學和相對論的邊界,我們可能對時空結構和引力舉辦前瞻性研究。”潘建偉說。
下一步,潘建偉希望在地月拉格朗日點上放一個糾纏光源,向月球和地球分發量子糾纏。通過對30萬公里或更遠距離的糾纏分發,來觀測其性質變化,對相關理論給出實驗測量。
“我早已47歲了,希望在60歲左右離休前,把這個實驗做完。”他說。
假如這個夢想能實現,潘建偉將摘取這個領域“皇冠上的明珠”。
潘建偉覺得,發展量子通訊、量子估算技術是國家重大需求,自己義不容辭,而把量子世界最奇怪的問題厘清楚,是自己內心的原動力。
“量子熱學為何會如此奇怪,這個基本問題根本沒有解決,我們可能還處于出發點上。對我來說,為何會有量子糾纏,是最深層次的東西,我一直沒有忘掉。我把實驗做下去,將來可能搞明白。”潘建偉說。
他也覺得,科學理論與實用技術不應被割裂,自己樂意竭盡竭力促使量子技術發展。
“用量子手段可以做好多事情,比如做原子鐘、精密檢測,甚至可拿來做腫瘤的初期確診。操縱好量子,將為人類帶來巨大福祉。”潘建偉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