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895年11月27日,一位飽經風霜的祖母在倫敦寫下了薄薄的一頁。 他去世后,他的家人在整理他的遺物時發現了這一頁。 也就是說,這一頁的幾十行字,已經獲得了當今世界享有盛譽的獎項——諾貝爾獎。 從1901年第一屆諾貝爾獎頒發至今,已經有100多年的歷史了。我們中華民族有5000年的文明,擁有世界1/5的人口。 迄今為止,還沒有臺灣科學家取得如此偉大的成就。 難道我們中國人真的很壞嗎? 不。 雖然在中國科學史上,曾有三位化學家僅在數學方面就取得了達到“諾貝爾化學獎”水平的重大科研成果。 遺憾的是,由于種種原因,他與諾貝爾化學獎一起去世,最終與他失之交臂。 這三位化學家分別是吳有訓、趙中遙、王淦昌。
>>>>
吳又勛的伯樂難求
吳有訓(正之)(1897~1977),廣東鳳城人,中國現代數學奠基人、教育家。 1920年畢業于北京高等師范中學(今北京大學前身)。 1922年1月,進入紐約學院深造。 就在這五年里,康普頓以訪問學者的身份在紐約學院從事研究和教學,吳友遜則跟隨康普頓進行化學方面的學習和研究。 1923年,他即將出任紐約學院院長,吳又訓即將成為他的研究生。 所以幾乎從一開始,吳又訓就和康普頓一起研究X射線問題。 1922年,康普頓在研究X射線量子散射時發現,當用單色X射線作為射線源對一些較輕的元素(如碳)進行散射實驗時,散射的X射線的波長由元素改變。 一些微小的變化,從經典化學的角度來看,這完全是一種反常的現象。 康普頓以他的名字將這些現象命名為“康普頓效應”。 康普頓選擇了量子理論來解釋這一異常現象,這就是他著名的 X 射線量子散射理論。
然而,這一發現并沒有立即得到化學界的廣泛認可。 一方面,這些效應與經典理論相沖突,另一方面,康普頓獲得的實驗證據并不充分,這讓相當多的研究化學家不敢貿然相信。 你基本上采取一種感興趣的觀望態度,等待進一步的實驗事實。 科學界對康普頓量子散射理論的質疑在于,他所依據的基礎實驗中實際上只有一個實驗樣本,那就是石墨樣本。 事實上,實驗本身完全沒有缺陷,但實際上只使用了一種材料,這使得很難解釋該效果的一般意義。
作為一名康普頓中學生,吳友訓的主要關注點就是否認康普頓效應的普遍適用性。 他設計了最佳的實驗方案,先后使用15種不同的樣品材料進行X射線散射實驗,結果均與康普頓理論相符,有力地證明了這一理論的廣泛適用性。 由于吳友遜高超的實驗方法,這種驗證工作無論在精度還是可靠性上都是無可挑剔的。 事實上,這種工作得到了康普頓本人的極為重視和高度評價。 他將吳有訓得到的15種物質的X射線散射譜和他自己的石墨散射譜收錄在他1926年寫的《X射線與電子》一書(該專著更名為《X的理論與實驗》)中。 -射線”,1935年重印時),被用作其量子散射理論的主要實驗證據。 康普頓在書中寫道:“實驗與理論的這些巧合并非出于巧合,圖III-48中的光譜(指吳友遜的15種物質的X射線散射光譜)就是證明;康普頓博士獲得的光譜就是證據。”吳友訓基于各種元素的散射與前述類似(參考他自己的石墨散射譜)。” 后來吳又訓在許多關于康普頓效應的專著中被引用。 光譜。
吳友訓對康普頓效應的主要貢獻是用公認的、準確的實驗澄清了日本耶魯大學著名X射線專家W. Duani及其助手GL Clark對康普頓效應的兩項指控。 據悉,吳友訓還對康普頓散射理論的發展做出了重要貢獻,那就是他用精確的實驗解決了康普頓散射中變化線與恒定線之間能量或硬度的百分比問題光譜。 這項工作立即引起了英國數學界的關注和重視。 1925年11月,德國化學會第135屆代表大會定于吳有訓實驗室舉行。 會議共宣讀或交流論文60篇,吳友訓的論文排名第一。 他的報告題目是《康普頓效應中變化線與恒定線之間的能量分布》。 這項工作被列為會議的重要議程,文章后來發表在英國《物理評論》上,這是該雜志1926年2月的第一篇論文。
康普頓效應發現和建立后,吳友訓親自參與了大量的實驗驗證工作。 1926年,他終于完成了題為“康普頓效應”的博士論文,并獲得博士學位。 獲得博士學位后不久,吳又訓收拾好行李,禮貌地拒絕了康普頓的挽留,踏上了回家的路。
康普頓因其對“康普頓效應”的研究而獲得1927年諾貝爾化學獎。 然而,為證明“康普頓效應”的正確性和發展“康普頓效應”做出重大貢獻的吳又訓卻因為沒有被提名為候選人而與諾貝爾化學獎失之交臂。 由于提名諾貝爾獎候選人的權利僅限于非常特定的人。 這些人可以分為兩類:具有永久提名權的人和具有特殊年度選拔權的人。 擁有永久提名權的人包括日本皇家理科大學的瑞典和外籍教授、諾貝爾化學和物理委員會成員、歷屆諾貝爾化學或物理獎獲得者以及來自美國和其他國家的教授。北歐國家。 各國(英國、芬蘭和瑞典)于 1900 年建立的科學院中的數學院士和物理學院士。 吳友訓當時只有30歲著名的國外物理文獻,名氣還不算太大,而且已經回到了祖國,所以根本就沒有被“提名”,所以無法被評判。 如果當時吳又訓被一位眼光獨到的“伯樂”“提名”,他就可以和老師分享1927年的諾貝爾化學獎了。
作為同時代的數學家,康普頓始終沒有忘記吳有訓對這一偉大發現的重要貢獻,并在他的各種專著和各種場合不斷提及吳有訓的實驗。 晚年他感慨地說:“吳有訓是他一生中最值得驕傲的兩個中學生之一,(另一位中學生是比吳有訓六年后獲得博士學位的LW阿爾瓦雷斯) ,1968年獲得諾貝爾化學獎,2009年)他應該獲得諾貝爾化學獎。”
1926年回國后,在北京大學學院教授近代化學和普通化學。 他十分重視實驗課程,指導了多名中學生的畢業論文工作。 他孜孜不倦地工作,孜孜不倦地教導別人,親自指導文獻復習,準備實驗裝置; 他以嚴謹求實的科學作風培養了許多優秀的中學生。
中國科學技術研究院成立于1958年,他多年擔任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副校長,盡管年事已高,仍親自教授研究院數學課程并致力于人才培養。 吳友訓在領導科學事業工作中依然認真負責。 他真誠地聽取各方意見,遵循好的意見,贏得了同學們的尊重。 他有膽識、有遠見,畢生志在中國科教事業。 他為中國科教事業的發展做出了巨大貢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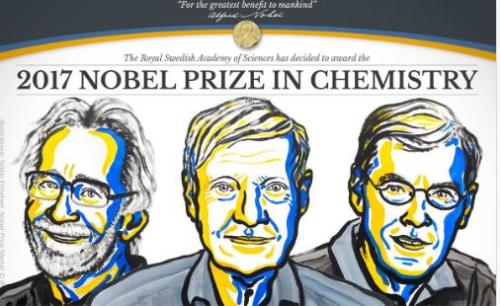
趙中遙的冤屈
趙忠堯(1902~1998),杭州桐廬縣(今蘭溪市)人。 我國核化學、中子化學、加速器和宇宙線研究的開拓者和啟蒙者,量子電熱學的重要奠基人。 1925年,從國立西南書院(今北京書院前身)畢業后,任教于北京大學學院。 1927年,趙忠堯赴日本加州理工學院深造,師從著名數學家密立根,獲博士學位。 1929年,趙忠堯在導師的指導下從事一項名為“硬伽馬射線穿過物質的吸收系數”的研究。 在做相關實驗時,他發現硬伽馬射線穿過鋁等輕元素時的散射完全符合已知的規律; 當它們通過鉛等重元素時,會出現異常吸收。 這一結果引起了他的注意,他將其寫成論文著名的國外物理文獻,發表在1930年5月出版的日本《國立科學技術大學學報》上。1930年9月,借助他自己制作的儀器,他從實驗中進一步發現,除了重元素對硬伽馬射線的異常吸收之外,還存在著一種以前從未見過的特殊輻射。 通過精確檢測這些特殊輻射的能量和輻射角分布,他否認了這些輻射是由質量與電子相當但帶有正電荷的粒子產生的。 這些粒子就是正電子,日本化學家狄拉克早在1928年就從理論上預言了這一點,科學家們仍在尋找它。 1930年10月,趙忠堯在日本《物理評論》上發表了他的重要發現。 趙忠堯無疑是世界上發現正電子的第一人,也是世界上第一個否認反物質存在的人。 而且,他進行的實驗是人類歷史上第一次直接觀察到正反物質湮滅所引起的現象。
這個發現是史無前例的,具有劃時代的意義,所以趙忠堯的發現震驚了科學界。 當時,很多人預測他會獲得諾貝爾獎。 而且,1936年日本皇家學會決定將數學史上偉大成就——正電子的發現授予諾貝爾獎時,并沒有頒給趙忠堯,而是頒給了趙忠堯。 日本化學家安德森觀察到了正電子軌道。 這里發生了什么? 多年來,人們有過各種各樣的討論和猜想,但仍然沒有人能夠解釋真正的原因。 因此,它成為科技史上的一個公案。
直到2000年,法國科技大學教授、諾貝爾化學獎委員會秘書G. 才向李政道博士揭示了這個謎團的答案。 原來,英國皇家學會曾真誠地考慮過授予趙忠堯諾貝爾獎。 沒想到,一位在美國工作的女數學家在一篇文章中報告了她的實驗結果,與趙中遙的觀察結果不同。 實驗結果的正確性受到批評。 這一事件在日本皇家學會引發爭議。 為了謹慎起見,他們決定放棄原來的意見,不再把諾貝爾獎頒給趙忠堯,而是頒給趙忠堯的朋友安德森,他也是發現了正電子。 幾年后,當人們否認趙中遙的實驗和觀察完全準確,而提出質疑的科學家因設備靈敏度不夠而造成錯誤的觀察時,已經太晚了。 就這樣,趙忠堯蒙受了極大的委屈,導致原本已經降臨到他身上的諾貝爾獎與他擦肩而過,成為諾貝爾獎史上的一大遺憾。
安德森在1983年出版的一本專著中也承認:當他的朋友趙忠堯的實驗結果出來時,他在趙忠堯對面的辦公室里,他意識到趙忠堯的實驗結果已經表明有一種對他的研究產生了啟發趙忠堯的研究成果,一種人們還不知道的新物質。 后來,G·埃克斯蓬教授在一篇文章中專門提到了此事,肯定了趙忠堯的歷史功績,并一度有些悲傷地表示,這是一個“非常令人不安、無法填補的偏見”。中國獲得諾貝爾獎。”
1937年,趙忠堯回國任復旦大學化學系主任。 他在我國首次開設了核化學課程,并主持建立了我國第一個核化學實驗室。 抗清戰爭爆發后,校園內移,趙忠堯先后在西北聯大、中央學院任教,期間培養了一批為我國原子能事業做出巨大貢獻的科研人才將來。
抗戰勝利后,趙忠堯擔任中央學院化學系主任。 他深感有必要在國外建立一個更好的核化學實驗室。 1946年,他受委托前往法國采購樂器。 由于國軍發動內亂,趙忠堯被迫留在法國,在麻省理工學院和加州理工學院從事核化學和宇宙射線研究。
新中國成立后,趙忠堯立志報效祖國。 1955年,他克服重重阻力,毅然回國參加中國科學技術大學近代化學研究所(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原子能研究所前身)的成立。 他利用回國時帶回來的加速器部件、儀器和實驗設備,先后于1955年、1958年建成我國最早的70萬伏和200萬伏質子靜電加速器,為我國核化學、加速器事業提供了支撐。技術、真空技術和離子技術提供了研究基礎。 在趙忠堯的領導下,研究所建成了核化學實驗室,領導了核化學研究。 他為新中國的核化學研究做出了巨大貢獻。
王淦昌的出生生不逢時
王淦昌(1907-1998),湖南省昆山縣人,我國著名核化學家,中國科學技術大學教授。 被譽為我國“兩彈之父”。 1929年畢業于復旦大學化學系。 1930年赴美國柏林學院留學,師從著名女數學家邁特納(Lise)攻讀博士學位。 當時的日本是國際數學的研究中心,許多世界知名的科學家聚集于此,開展核化學的各項研究。 1930年,兩位美國人波特和貝爾用放射性物質發出的帶電粒子轟擊輕金屬鈹時,發現放射出一種穿透力極強的射線。 由于這些射線不帶電,包括邁特納在內的許多科學家認為它是具有巨大能量的伽馬(gamma)光子。 時任邁特納實驗助理的王淦昌對此表示懷疑。 因為他通過計算知道,伽馬光子無論如何都不會有這么大的穿透力。 他建議使用一種稱為“云室”的儀器來研究和確定這些未知射線的性質,但梅特納兩次都反對。 后來,1932年2月,年輕學者查德威克在美國利用“云室”重新做了上述實驗,并否認未知射線不是伽馬光子,而是一股中性粒子流。 他把這些中性粒子稱為中子。 1935年,查德威克因發現中子而獲得諾貝爾獎,但王淦昌卻因導師的阻撓而失去了獲獎的機會。
抗清戰爭時期,王淦昌在福建書院任教。 由于動亂,中學屢次西遷,王淦昌過著半生無家可歸的生活。 當時的教學和實驗條件十分困難。 但即便在這樣的情況下,他也沒有一刻放棄對化學的研究。 通過閱讀西方學術期刊,他發現美國化學家正在尋找一種轉瞬即逝的基本粒子——中微子。 由于方法不當,所有對中微子產生印象的嘗試都失敗了。 王淦昌是一個善于動腦子的人。 憑借豐富的知識和非凡的智慧,他經過反復思考,提出了利用K電子壓印中微子的獨特實驗方案。 而在當時動蕩不安的中國,根本沒有條件完成這個實驗。 無奈之下,他只好寫成論文《關于尋找中微子的建議》,于1942年1月發表在英國權威期刊《物理評論》上。1947年,王淦昌發表了《建議探測中微子的幾種方法》在“物理評論”中。 不久之后,德國化學家艾倫聽說了這件事。 根據王淦昌提出的實驗方法,實驗否定了中微子的存在,一舉獲得了諾貝爾獎。 王淦昌再次無緣諾貝爾獎。
1960年,王淦昌在前南斯拉夫杜布拉國家原子能研究所工作時,發現了一種新的帶負電超子“反西格瑪負超子”。 當時,這是世界上第一個在實驗室發現的帶負電的超子,這一發現至今仍被列為杜布拉國家原子能研究所成立以來最重要的發現之一。 諾貝爾獎級別的重大科研成果。 遺憾的是,由于當時正值中蘇關系惡化的特殊時期,王淦昌又失去了獲得諾貝爾獎的機會。 就這樣,王淦昌三次與諾貝爾獎失之交臂。

1960年代初,二機部領導找他談話,調他參加原子彈的研制。 他當即接受,并要“以身許國”。 王淦昌教授懷著強烈的愛國主義情懷,始終對國家任務抱有高度的歷史使命感和責任感。 此后,他隱姓埋名20年,放棄了多年從事的基礎研究和大城市相對良好的工作生活條件。
1964年,他與南斯拉夫著名科學家巴索夫獨立提出了激光慣性約束核聚變新概念。 他是我國慣性約束聚變研究的奠基人。 積極推進高功率激光化學聯合實驗室建設,仍指導慣性約束核聚變研究。 積極指導原子能研究所開展電子束泵浦氯化氫激光器等研究,1982年獲國家自然科學獎銀獎,1985年獲國家科學技術特等獎兩項進步獎。
盡管由于種種原因,上述諾貝爾獎從未頒發給我國,但這三位大師的偉大成就和研究成果卻永遠載入史冊。 因為他們為人類化學的發展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光明的未來
關于中國何時獲得諾貝爾獎的問題,恐怕楊振寧先生已經做到了。 他說:“我認為20年內,中國將會出現諾貝爾獎級別的工作。如果經濟增長快的話,不會有一個,而是幾個。因為中國經濟增長很快,但中國領導人有非常多的工作機會。”對技術發展速度的殷切要求,研究投入大幅下降。”
一個科學波動周期約為35年,任何一個科研體系沒有嚴重缺陷的國家都有可能在這段時間內獲得科技研究的重大突破。 按照這個推論,如果從1978年的“科學之夏”算起,到2013年還有35年,最多還要再等幾年。 中國大陸不缺科學精英,應該實現諾獎為零的突破。
這只是一個大膽而開放的預測。 愿我們打破禁錮人才產生和成長的制度堅冰,打破學術孤島,營造和諧良好的科研環境,力爭讓諾貝爾獎提前三天在中國大陸誕生。
參考:
1.(美)羅伯特·馬克·弗里德曼,楊建軍譯。 《諾貝爾科學獎的陰暗面》[M]. 北京:北京科學技術教育出版社,2005年8月,第一版
2.張九清,《牛頓以來的科學家——現代科學家群體的視角》[M]南寧:廣西教育出版社,2002年
3.楊振寧,《六年讀書與教學()楊振寧筆記》。 臺灣:時代文化出版社,1995年10月15日
4.郭以嶺、沈惠君主編的《吳友訓選集》[C]。 廣州:湖南科學技術出版社,2004
5.胡濟民等。 王淦昌及其科學貢獻[M]. 上海:科學出版社,1987。
6、薛冬、劉振坤,中國諾獎僅一步之遙[N],光明晚報,2000年8月7、中國科學院新聞網科教視點>>科技前沿[EB/ 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