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中國實驗室里,繼鐵基超導、多光子糾纏、中微子振蕩后,我國數學學再獲突破性進展。1月8日,由復旦學院院長、中國科大學教授薛其坤領銜的復旦學院和中科院化學所實驗團隊在量子反常霍爾效應取得的突破性成果,獲得2018年度國家自然科學獎銀獎。
全球首次發覺:中國實驗室里形成的世界級基礎研究原創成果
“量子反常霍爾效應”——當第一次據說這個名子,許多人就會一頭霧水。但是,走入這座自由王國,人們會發覺一棟迥然不同的摩天大廈。由于薛其坤團隊的發覺,中國標明了這座大廈的新高度。
微觀世界的運行由量子熱學規律支配,會顯示完全不同于宏觀世界的現象。霍爾效應是一種常見的電磁現象,廣泛應用于磁傳感和半導體工業。這么當量子反常霍爾效應出現,會形成如何的神奇?
科學家們覺得物理實驗霍爾效應,量子反常霍爾效應的最美妙之處是“不須要任何外加磁場就可以實現電子的量子霍爾態”。因而物理實驗霍爾效應,這項研究成果將會促進新一代的低煤耗晶體管和電子學元件的發展,可能加速推動信息技術革命的進程。
據介紹,量子反常霍爾效應,可以改變電子的運動軌跡,使其像在高速道路上行駛的車輛一樣有序,降低了中間阻撓,增加了電子運動中的能量耗損。
這一發覺經轉化應用,對普通大眾來說,最直接的影響就是有可能會解決手機或筆記本發熱、耗電快、運行慢等問題。
自1988年日本數學學家提出可能存在不須要外磁場的量子霍爾效應以來,不斷有化學學家發表各類方案,但在實驗上并沒有取得任何實質性進展。2008年,薛其坤帶領團隊開始步入這一領域,經過四年研究,總算在世界范圍內首次觀測到量子反常霍爾效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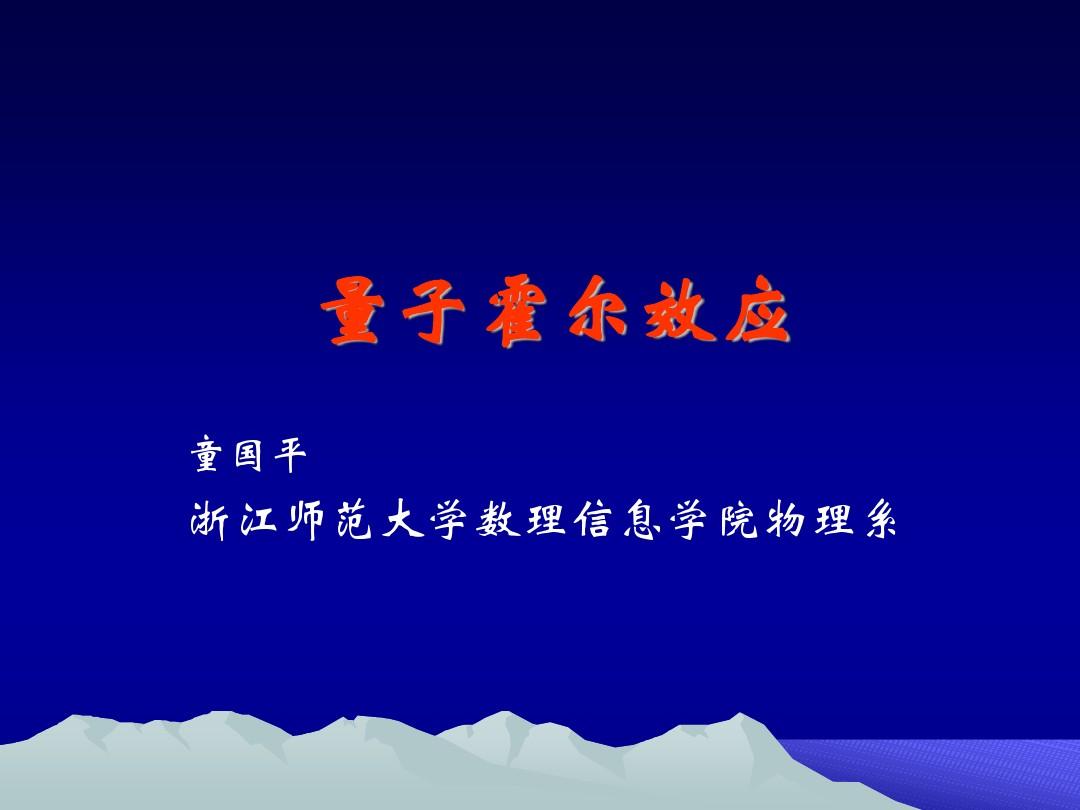
這是世界數學學界近些年來最重要的實驗進展之一,推動了國際學術方向。這一發覺的論文在英國《科學》雜志發表后,諾貝爾獎獲得者楊振寧稱:“這是從中國實驗室里,第一次發表出了諾貝爾獎級的數學學論文!”
創新實驗方式:學術公路前行每一步都有意義
從沂蒙山區走下來的薛其坤,個子不高、鄉音濃重,樸素而詼諧。拼搏與執著,是他和團隊成員王亞愚、何珂、馬旭村、呂力等在科學之路上的人生信條。
薛其坤研究團隊常年以來結合分子束外延生長、極高溫強磁場掃描隧洞顯微鏡、角區分光電子能譜技術,在表面、界面、低維化學學領域作出了國際一流的工作。
2008年,薛其坤研究團隊捉住拓撲絕緣體這個新領域盛行的抓手,在國際上率先構建了拓撲絕緣體薄膜的生長動力學機制,借助分子束外延生長出國際最高質量的樣品。所提出的生長方式現已成為國際上通用的拓撲絕緣體樣品制備方式。
在此基礎上,她們借助掃描隧洞顯微鏡闡明出拓撲絕緣體表面態的拓撲保護性和朗道量子化等奇特性質。該研究團隊與國外相關科學家的努力促使中國在拓撲絕緣體領域研究中處于國際領先行列。
“這是過去二十多年來匯聚態化學和材料化學領域,最具挑戰性的實驗之一。”薛其坤直言,實驗的難度在于目標的不確定性,“我們所要實現的材料如同一個人既須要田徑運動員的速率、又要有田徑運動員的力量、更要有花樣溜冰運動員的方法”。
“我們的實驗結果得到了科學界的重復驗證,量子反常霍爾效應的實驗經受住了歷史的考驗。”薛其坤說,“想在科學原創上發覺他人看不到、發現不了的東西,肯定你的耳朵要更亮,你使用的儀器工具碼率、靈敏度必需要更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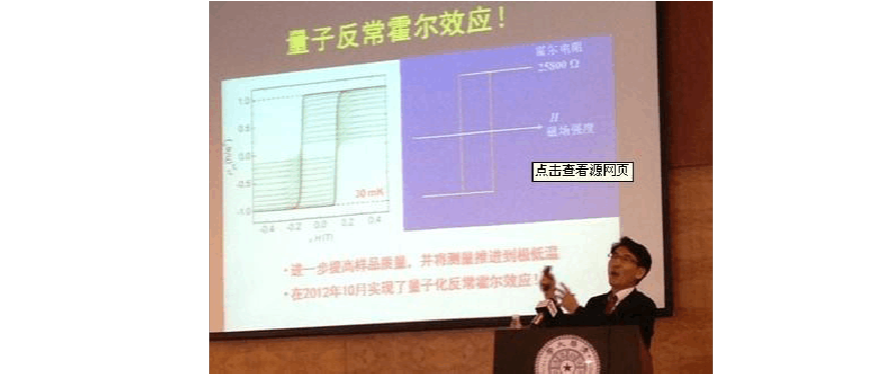
量子反常霍爾效應和低溫超導是數學學界最熱門的兩個課題。薛其坤早已完成了后者,下一步將朝著前者進發。他直言這是一次嶄新的嘗試:“在學術的公路,前行的每一步都有意義,這就是科學的魅力。”
理解“物理之美”:中國基礎科研正處“黃金時代”
科學探求就是無數次接近真理的過程。現今的薛其坤,越來越深刻地理解了“物理之美”。他覺得,自己的生活每晚就是回答為何,找尋謎底的過程讓他樂此不疲。
“我們的成果與變革開放40年來取得的成就密不可分。”薛其坤說,量子反常霍爾效應的發覺是變革開放40年間我國在基礎研究上的一個重大成果,日漸強悍的國力、良好建立的科技新政、科學系統的科技規劃、催人奮進的創新氣氛是基礎和保障。
發覺量子霍爾反常效應團隊的五位主要完成人,平均年紀48歲,她們瞄準同一重大科學目標,各有校長但相對獨立,單元科研團隊的成員間產生了高效合作,其深度和持久性在國外外也不多見。
人類的生命稍縱即逝,物質也會隨著時間湮沒,惟有不朽的知識閃亮在歷史的長河里。團隊成員們表示:“中國的基礎科研正處在一個黃金時代,能成為這個時代的拼搏者,感到幸福。”
薛其坤覺得,必須讓創新人才坐得住冷板凳、耐得住孤寂,在基礎研究、原始創新上不斷突破,筑牢國家核心競爭力的基石。
“我們是黨和國家培養上去的科學家。新時代為我們提供了更好的機遇,我們定要不負使命、努力拼搏,為國家強悍、人民幸福和科學探求不斷作出新的貢獻。”薛其坤和他的朋友們壯志滿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