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華社上海6月19日電(記者屈婷、全曉書、喻菲)這是中國空間科學的“光榮時刻”:硬X射線調制望遠鏡(HXMT)被穩穩放置在太空,將展開對銀河系的巡天掃描,去探究最前沿、熱門的宇宙之謎:黑洞、脈沖星、伽馬暴……
這也是一群高能天體化學學家夢想成真的時刻:作為中國空間科學先導專項中最貴、最重、科學儀器最多的衛星,HXMT將改變空間高能天文研究常年依賴美國衛星觀測數據的狀況。
《科學》雜志的記者曾在訪談中問HXMT首席科學家張雙南當初為何選擇歸國,他回答說:“在國內的教科書上看不到中國科學家的貢獻,這讓我很難過,我要改變這些狀況。”
這句話幾乎是三代中國天體化學學家在近百年歲月里的“標準回答”。正是她們用智慧、青春乃至生命培植的“沃土”,讓這顆負笈西學求來的“科學種子”不斷出芽、生長:塊莖追逐著物質世界最微小的粒子,樹干指向以光年估算的宇宙大尺度觀測。
星辰大海路迢迢,參天小樹待長成。
“我們有何澤慧!”
何澤慧
HXMT衛星被命名為“慧眼”,不僅蘊意著中國在太空“獨具慧眼”以外,同時也為了記念中國過世核化學學家何澤慧教授。
在HXMT立項面臨困難的情況下,2009年5月和8月,正是何澤慧兩次致信國家領導人,懇請關心HXMT項目,“使我國捉住借助方式的原始創新,在一個新的領域取得突破的機會。”
原先天體物理學的發展,上世紀七八十年代發射的X射線太空望遠鏡普遍采用一種高昂、復雜的編碼成像方式。這些方式除了斥資巨大,并且須要制造出工業上接近光滑極限的鏡面,這是當時的中國做不到的。
在這些情況下,年青的化學學家李惕碚和吳枚在90年代初提出一種名為“直接譯碼”的成像方式,借助簡單的準直偵測器掃描數據才能進列寬幀率成像,并基于此提出了HXMT的設想。
然而,這些新方式在提出之初由于“太過神奇”,甚至被懷疑是“弄虛造假”。經過六年左右的理論、實驗和數據剖析工作,“直接譯碼”方法才被國外外學者漸漸接受。
但何澤慧幾乎是第一時間就給與了竭力支持,這件事讓78歲的中國科大學教授、清華學院天體化學中心所長李惕碚感念至今。他說,支持一個全新的研究領域,對何澤慧這樣成就卓著的科學家是要冒“丟臉”的風險的。
何澤慧是一位化學學界的“奇男子”,也是中國科大學第一位女教授。她和“兩彈一星”元勛錢三強是中國近現代科學界聞名世界的伉儷。
1973年,中國科大學高能化學研究所組建后天體物理學的發展,何澤慧兼任副校長。1978年,所里一些年青人提出想舉辦空間天文觀測。何澤慧一聽就興致盎然,覺得這是一個全新的科學“生長點”。
上世紀80年代,這批年青化學學家用高空汽球,搭載空間硬X射線偵測器去舉辦觀測。何澤慧的中學生馬宇蒨和姜魯華記得,每次領取汽球時,多在七、八月,天氣十分悶熱,但何澤慧每場必到,短則幾小時,長則半天,以示支持。
她最為看重學術思想的創新。李惕碚追憶:“當‘直接混頻’成像方式取得初步成果的時侯,何澤慧和錢三強先生就來到實驗室了解相關情況,給我們以熱情的鼓勵。”
年少時,何澤慧立志“靜默地想辦法救國”;在聲名鵲起時,她決然回到百廢待興的新中國;到了她為人旅長時,在每一個科學探求的“關鍵時刻”,李惕碚說:“我們有何澤慧!”
“第一顆衛星,我們要盡量自己做”
從1993年提出HXMT衛星的構想,到2011年即將立項,18年過去了。“基于掃描觀測和‘直接混頻’成像方式的大天區、高靈敏成像技術優勢依舊存在!”李惕碚用一切機會和渠道,到處解釋和倡議。
他的中學生、HXMT衛星有效荷載總設計師盧方軍看見“老師這么大歲數還在為這件事操勞”,也中斷在日本的博士后研究,選擇即將加入HXMT項目。
盧方軍
同樣,當李惕碚提出希望張雙南能幫助他研發這顆衛星時,早已在NASA工作并成為“學術新星”的張雙南欣然回國。
作為一顆復雜的空間科學衛星,HXMT研發的每一步都飽嘗艱辛:偵測器頻頻被污染、電子學系統工作失常……引發這種問題的誘因常常纖毫如發,排查和解決要花去數月甚至半年以上的時間。
這其中,好多都是自主研發帶來的問題。作為國產化的積極倡導者,盧方軍直言,自主研發不是一條捷徑,非常是在國家工業水平還比較粗放的條件下“白手起家”,會遭到好多意想不到的困難;并且從學科發展和實驗室建設的角度來說,卻是十分有價值的。
例如,在衛星打算裝機上天的“正樣”階段,就發生過一次重大“險情”:衛星上的高壓模塊在嚴苛的空間環境篩選試驗中,可能由于反復的熱脹冷縮造成焊點“疲勞”開裂,導致功能損壞。如何修?連生產模塊的日本廠家也不曉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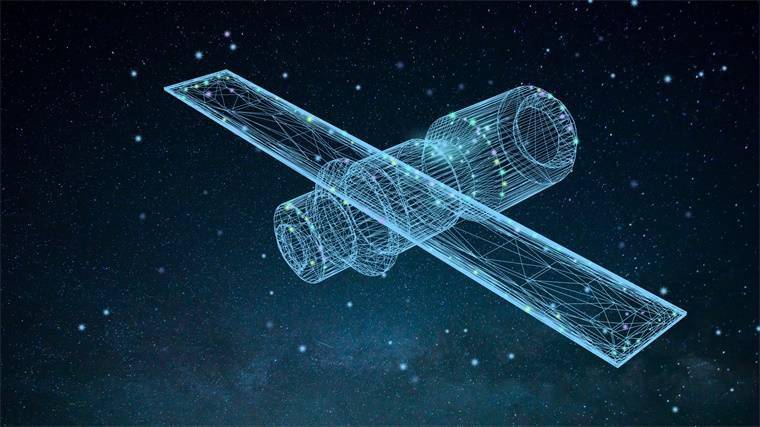
眼看一個細節就要造成長時間的延后,不理解的聲音也驟然而至。“當時十分著急!”盧方軍追憶說,但HXMT衛星有效荷載總工設計師徐玉朋“特別冷靜”,找了各類各樣的資料進行研究,最后嘗試把高壓模塊上的一些“硬聯接”變成“軟聯接”,總算解決了這個問題。
“第一顆衛星,我們要盡量自己做,先把套路熟悉了,之后的衛星再去考慮國際合作。否則,一上來就合作,他人說哪些是哪些,我們都無從判定。”盧方軍說。
“這顆衛星,是一生中值得回首的山峰”
從起草項目建議書到組織任務施行,盧方軍“日夜都在尋思,常常整夜睡不著覺”。結果,連續的疲勞和“排山倒海般的壓力”使他兩次患上了蕁肺炎,一到天熱就得病,必須服藥就能控制。壓力最大時,盧方軍“一個人背著單反背著水,在山里轉悠”,以攝影來緩解身心。
在他的辦公室里,大概400年前一顆星體爆發后留下的遺跡被復印成兩張色調艷麗的圖片,靜靜地貼在椅子上方,如同時刻提醒著主人不要忘掉那開在宇宙深處的花朵。
HXMT衛星的中能望遠鏡團隊自主研發的硅—PIN偵測器性能達到國際先進水平。
在接手HXMT項目之前,盧方軍仍然在做超新星遺跡的研究工作。中斷在日本的博士后研究回去時,一些科學家同行勸告他不要做硬件,囑咐他研發儀器周期太長,會耽擱科學產出。
事實上,在為HXMT繁忙的日子里,盧方軍的確無瑕顧及原先的研究課題,只是零零星星地發表了幾篇論文。
HXMT上天后要發揮作用,還有賴于一項重要的“標定”工作。哪些是“標定”?中低能X射線標定裝置校長設計師陳玉鵬打了一個比方,就好比給偵測器的各項性能提供一把“標尺”,這樣全球科學家能夠按照它來“修正”觀測數據,提升觀測精度。
因為X射線的光斑很小,只能把偵測器一點一點地對準光斑,每次標一個象素點。每位象素點,要測30個能量值。對于HXMT如此遼闊的波段范圍,工作量之大可想而知!雖然早已做了簡化,這項冗長而精細的基礎工作,陳玉鵬和團隊一做就是3年。
“從個人來講,其實是有點吃虧。”盧方軍說,但發表文章帶來的個人成就感是難以和這顆衛星的成功相提并論的,由于前者匯聚了幾代科學家的努力和一個團隊持續十幾年的拼搏,對中國高能天體化學的發展有著重大意義。
“這一輩子,當你回望舊事的時侯,看得見的是山峰,而不是平地。HXMT,肯定是我人生中的一座山峰,并且是迄今為止最高的山峰。”盧方軍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