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智元導讀】在年度十大熱文中,讓我們看一看:這種博士有哪些煩惱,我們能汲取哪些樣的經驗。
隨著2022年接近尾聲,整理出了2022年閱讀量最高的十大熱文,其中包括博士們經歷的令人失望的筆試、非常規的實驗室大會、職業轉折等等。
在昨天的第二彈中,讓我們來瞧瞧,這幾位博士的故事。
天體化學學,讓我接受了自己是雙性戀
從小,我就愛問問題:為何太陽是紅色的?為何天秤看上去是那樣的?為何土星有一個點?
我的媽媽回答了她們能回答的問題,不能回答的,她們就買書給我看。
但從我5歲左右開始,我最常問的問題就是:為何我是男生?
我的父親難以回答。
在1990年代的阿巴拉契亞山脈腳下,沒有人有過這樣的問題。這是我第一次遇見沒有簡單答案的問題。
直至上小學,我才逐漸停止問這個問題。青春期讓我失望和痛恨。
每三天,我都突顯出越來越多的男性干練,這讓我倍感越來越孤立。
在學術方面,情況也好不到那里去。
在小學時,我非常厭惡化學課。它僵化的規則雖然反映了我所生活的社會。
如同期盼鐘擺擺動、方塊滑下斜坡、球從斜坡上掉出來一樣,我認為我應當去修道院,遇見一個女人,離婚生子。
這些看似難以逃避的軌跡,讓我對這個世界倍感失望和僵硬。
我上學院是由于我想逃出。我倍感漫無目的、空虛、毫無意義——但與此同時,我正站在一個十字路口,通向1000種不同的未來。
如同完美圓球上的粒子一樣,我可以朝任何方向倒塌。
那三天,純屬碰巧地南京大學天體物理學,我走入了一家書城,在前臺的椅子上見到了史蒂芬霍金的《宏偉設計》()。我不曉得那一刻是哪些神奇的魔力,讓我拿起了一本關于宇宙學的書。
但這的確發生了,在短短的幾分鐘內,我發覺了通向新數學學的房門——一種不一定有答案的數學學,一種與自身不一致的化學學,一種是零亂、混亂而有趣的數學學。
一禮拜后,我轉入了天體化學學專業。
在接出來的幾年里,我了解了相對論,以及在適當的情況下,時間本身是怎樣變慢的。
我了解了量子熱學,在那兒任何事情都可能發生。
規則不再是絕對的。我覺得是事實的東西,實際上只是對不可知事實的近似。
在學院里,我第一次看到「變性人」這個詞。我遇見了戀愛關系中的酷兒。
這與我第一次接觸到的酷兒迥然不同——我13歲時,的成員掄起著口號,來到我的故鄉進行游行。
在學院結束時,我意識到,我是雙性戀——和其他人一樣,我被自己的性別所吸引,如同萬有引力將宇宙中的每一個事物都吸引到另一個事物上一樣。
這些覺得很自然,如同我找到了一種較低能量的存在狀態。并且我一直沒有處于能級。
我找到能級時,我的研究生學業正進行到一半。
當時,我通過上的同學,發覺了「非二元性」()這個標簽。
是的,就是這個詞!它的流動性,和對傳統雙性系統的否定,這些覺得太對了!我如同找到了家一樣。
那覺得如同,我花了一生的時間企圖解決一個混亂的系統,卻發覺它的答案不是一個,而是好多。
就在那時,我意識到我是一個光子——擁有二元性任何一方固有的品質,但最終并不屬于任何一方。
「非二元性」的生活并不總是這么容易。
有一段時間我過著雙重生活,在互聯網上,我是真實的,在讀銀華,我的身分就隱藏上去。
然而當我打算好時,我選擇接受我的身分,這將我帶入了一個不可思議的圈子。
如今,我意識到了我的身分具有的力量。
非二元性意味著,每天都要接受挑戰。這意味著一切都可以遭到指責,并且必須遭到指責。這意味著從新的角度、以新的方法,去探求他人覺得理所其實的事物。
在我的日常生活中,我的性別認同,促使我找尋特別規的方式去解決困局。
我掀開看不見的石頭。我嘗試非正統的方式。我與重大的、基本的問題作斗爭。
所有那些都讓我成為一名更優秀的科學家。
化學學總是在發展,性別也是這么。
當我們了解事情比表面上看上去更復雜時,我們才會學習。
當科學家接受宇宙的復雜性時,我們的科學只可能進步。
論文專著者中,沒有我
讀銀華,一個同學提議我們合寫一篇論文,我當時很激動。
我征詢了碩導的意見,他同意了,并且建議我說我們應當在開始前確定我們各自預期的貢獻,和名子的排序。
我沒有聽從他的話,由于我不會和我的好同事磋商。
我相信,他會給與公允的待遇,我不想給他人留下斤斤計較的印象。
一切都很順利,我們共同完成了論文,把它發出去了。
好多年過去了,我已經忘了導師的建議。
后來我成了助理院長,我曉得,發論文對我的職業生涯是至關重要的。
由于我沒有資金或項目來招收自己的研究生,所以我和其他同學共同指導她們的中學生。由于我在科研過程中出了力,所以是論文的專著者。
我和朋友們對這些多贏的局面都很滿意,一切仿佛都很順利——直到我到了另一個機構。
離開幾個月后,我在瀏覽文獻時發覺了一篇由我和朋友共同指導的中學生發表的新文章。見到我沒有被列為作者,甚至沒有被提及,我倍感驚訝和沮喪。
我把這件事告訴了另一位論文指導,他當時是我的好同事。他告訴我,她們忘掉了我的貢獻,但我對此表示懷疑。這篇論文的其他許多譯著者,雖然都沒有對這項工作有多少貢獻。我們難以達成愉快的解決方案。
自此,我們再也沒有合作過,我們的關系焚毀了。多年過去了,我幾乎忘掉了這段不快的經歷,我把它當成一次不幸的碰巧口角。
此后,我在許多不同的國家和機構中,繼續精進我的職業生涯。以前有一段時間,我所在的機構有足夠的資金和中學生南京大學天體物理學,我正是團隊的一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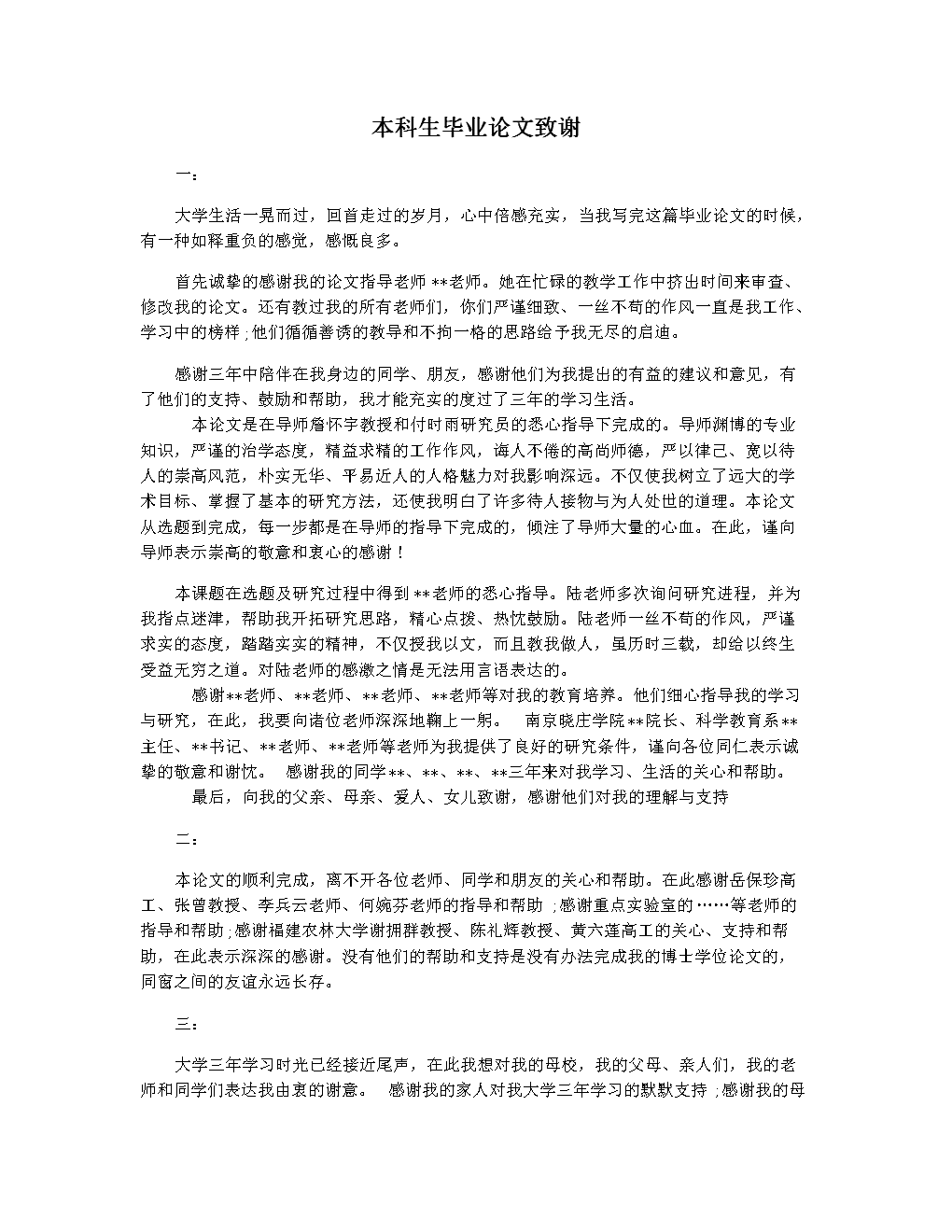
我們的團隊達成一致:團隊發的所有論文,就會署上每位團隊成員的姓名。事后看來,這不是一個好方式,由于有一些作者做的貢獻極少,卻獲得了同樣的榮譽。
但那時,我們對此還沒有成熟的認識。
在接出來的幾年里,我和朋友們都去到了不同的機構。
我注意到,我的朋友們再發表我們以前合作的論文時,都不再署上我的名子。我以為你們都默認了這個合同,所以我再發論文時,也不會署上她們的名子。
所以,當我接到其中一位朋友的電話時,我很震驚,我沒有把他列為專著者,這讓我倍感不安。我企圖向他解釋,但他認為很委屈。
以前,我也處于他的位置,那時我倍感遺憾,飽含懷疑。
在每次這樣的爭吵中,到底是我錯了,還是我的朋友錯了?
接出來的幾天里,我告訴自己,我在這兩種情況下都沒有做錯——直到有三天,當我晚上在海邊遛彎時,我的導師多年前的建議閃現今腦海中。
「Naim——你可以跟人合作,但首先要說好你的角色,和分配的榮譽。」
我意識到:在這兩種情況下,我都犯了同一個錯誤:我應當從一開始就與我的朋友講清楚,作者身分是如何分配的,無論我們之間的友誼怎么。包括后續的情況,我們也該明晰商量,包括有人換機構的情況。
值得幸好的是,通過深入的攀談,我修補了與第二位朋友的關系。
從那時起,我改變了與人合作論文的形式。
在開始一個項目之前,我必將會展開討論,以明晰每位團隊成員的角色和預期的榮譽,但是承認每位人的貢獻可能會在項目過程中發生變化,在這些情況下,我們可能須要重新考量我們的合同。
有時我的朋友們看上去很吵架,似乎我是一個冷酷的職場人士,根本不把她們當同事。這讓我喪失了幾個潛在的合作機會。但苦悶的經歷一次又一次地告訴我,這是最好的辦法。
只有用這個辦法,能夠推動常年合作、確保每位人都得到應有的榮譽,并最終保護好我們的個人關系和職業關系。
我如此優秀,研究生項目為何會拒絕我?
我從事研究生招生工作將近20年,但得獎的候選人就是最優秀的嗎?
定義所謂的理想候選人的標準不是一成不變的。這個過程可能是不公正的,實際考慮也發揮了作用,首先是項目資金和咨詢能力有限的現實。
無論哪種方法,拒絕的誘因常常與院長和項目有關。以下是拒絕優秀候選人的五個理由:
對于來自邊沿化群體的中學生來說,研究生投檔的結果尤其無法預測。
偏見是一個主要的、多方面的問題——這就是為何班主任應當反省和討論她們的投檔優先事項,了解當前關于選擇和偏見的研究,并制訂共同的標準。
我曾在委員會中處于令人不安的窘境,由于她們拒絕了成績優異、研究經驗豐富和個人陳述有力的候選人——僅僅是由于她們的研究興趣與教員的具體、直接的需求不一致。
優秀的申請人常常被拒絕,由于班主任除了考慮某些中學生,并且考慮她們想要招收的群體。
想要平衡是很常見的——被投檔的中學生群體在好多方面都是不同的,包括她們的社會身分和研究興趣。
我以前觀察到招生委員會拒絕了來自一所一流學院的申請人,該學院擁有7篇第一作者的出版物。
院士們十分確信他會被排行更高的項目投檔,以至于她們不想冒險給他投檔。相反,她們接受了她們覺得更有可能出席的申請人。
假如兩位院長熱衷于為同一位申請人提供建議,但是沒有共同建議的結構,這么院士們可能會通過簡單地拒絕申請人而不是爭執來保護彼此之間的關系。合作是學術界的一種美德,但它并不總能使中學生獲益。
投檔決定不僅僅涉及對申請人的價值和潛力的判別。假如你是每年收到拒絕信的成千上萬的準研究生之一,其實這篇文章可以幫你找到適宜自己的offer。
參考資料: